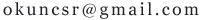两千年来有关孔子思想的论述卷帙浩繁,这里只就若干主要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孔子儒家思想的分化和不同学派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统治者都竞相礼聘懂得《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的儒生,以便在政治、外交、日常生活等各方面为他们出谋划策以至帮忙和帮闲。因此,儒家学派有了很大发展。孔子弟子中有很多人在孔子死后也都开始收徒授业,于是孔门后学也就越来越多,对孔子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也越来越有差异。孔子弟子出身不同、阅历不同、造诣不同,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各执己见、各立门户,相互指责的情况屡见不鲜。从《论语》下述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子游日:“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未也。本①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 “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倦作传解──作者注) 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②这里子游、子夏所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是教门人弟子以“君子之道”先从何处人手的问题。子游批评子夏有末无本,或重末轻本,子夏不同意子游的责难,而认为哪个应该先教,哪个应该后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子夏的意见和孔子“因材施教”,“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等似较近。在《论语》等书中像这类相互指责的话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由于儒家内部观点不同、相互指责,逐步形成了一些打着孔子儒家招牌而相互对立的派别。《韩非子·显学》篇指出:“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 有孙氏(即荀卿──作者)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便是所谓儒家八派。此外,荀子也曾经批评过“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等等。在这些儒家派别之中,只有以祖述孔子为己任的孟轲和荀卿为代表的两派,在一定程度上对孔子思想既有所阐述,也有所补充。发展和修正。如孟子在君民关系上,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一“民贵君轻”思想不仅大大发展了孔子思想,而且是在封建社会中敢于提出的民主思想的可贵萌芽。在君臣关系上,主张相互尊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特别提出道德高于王权,王者必以大人为师的观点, 他说:“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 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他甚至认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对孔子“忠君尊王”思想的重大修正和发展,十分可贵。这些言论曾引起一些专制暴君的反感,例如朱元璋就曾命令御用文人删除这一类文字,甚至企图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子游这里讲的“本”主要是指仁、礼等而言。荀子在“隆礼”的基础上既重视利,也重视义,一面强调努力耕战以加强国家实力,一面又强调推行王道以争取民心。他说:“传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这些思想既没有孔孟仁义礼乐的迂远疏阔,也避免了法家严刑峻法的残刻寡恩,集中两者的优点,为地主阶级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礼治理论。荀子的学生李斯、韩非把他的学说运用于秦国,使秦完成统一大业;但他们片面地发展了荀子思想,提出专任法、术、势的法家理论,导致了秦朝的速亡。为了论证自己的礼治思想,荀子提出新的天道观,认为天即是自然,它有自己运动的规律,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 让自然为人类服务。他还提出“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抗,由性恶强调礼法的规范作用和对人进行教育的必要性。其实,孟子主张性善, 荀子主张性恶,两人都是各执一端,都不符合孔子提倡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精神。可以看出,孔子在性善、性恶这个问题上站得更高,看得更深,因为对任何人来讲,性善或性恶都不是天生的,善和恶归根到底决定于后天环境和教育。由此可见,当时孔子儒家思想这两大学派,其中孟子除了对孔子思想有一定补充和发展外,更多的是遵循孔子思想的基本原则;而荀子除了遵循孔子思想主要原则外,更多的则是对之有所补充、有所修正、有所发展。这是孔子思想分化和建立不同学派的开始,而以后的分化和学派的建立陆续发生,其中包括两次对孔子思想的大篡改。
第二,“独尊儒术”和对原始孔子思想的第一次大篡改历史是常常以讽刺性的戏剧形式出现的。向汉武帝提出并被接受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是“为儒者宗”的今文经学派儒者董仲舒,而第一次大篡改孔子思想的也正是这位董仲舒。董仲舒对原始孔子思想的大篡改, 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问题上:
1.“三纲”、“五常”是天意所决。前已指出,孔子一贯主张的“忠君尊王”思想是维持和巩固封建君主宗法统治的思想支柱,这是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同时也是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产物,但这里并没有天命神鬼这类的话夹杂其间。孔子思想中的君臣、君民关系还保留着一定的君臣、君民相互尊重的原始民主精神,而这一精神则完全被董仲舒糟踏和篡改了。董仲舒把当时人间最重要、最普遍的三种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所谓“三纲”,这完全是一方绝对顺从另一方的主奴关系。为了证明“三纲”是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董仲舒又请出天来助长声势,他说:“王道之三纲, 可求于天。”这样,董仲舒就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三纲”是天意所定, 不允许人作任何改变,用天意把这三种关系纳入极端封建专制的框子里去了。在这“三纲”中,君臣关系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纲,他明目张胆地说: “《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②并以天的名义宣布“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即君王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君臣的关系是如此,父子、夫妇关系也类此。这种阴森森的“三纲” 关系不是对孔子前面所提出的君臣关系中一些原始民主精神和父慈子孝、夫
义妇听的父子、夫妇和顺关系的歪曲和篡改吗!董仲舒生于孔子死后三百余年,这期间科学文化和社会经济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他对自然、对天的了解理应比孔子要多些,理应比孔子思想有所前进,但实际上却比孔子还大大倒退了。例如对于“天”,孔子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很少谈天,而董仲舒则大谈其“天人感应“,并且认为“三纲”乃天意所决。这难道不是董仲舒异想天开、随心所欲地篡改孔子思想而强不知以为知地妄谈“天”吗! 董仲舒的所谓“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前四个仁、义、礼、智原是孟子所讲的四德,董仲舒为了符合神秘的五行之说,加上一个信。其实,如前所说,仁、义、礼、智、信都是孔子仁的人生哲学中的部分德目, 孔子完全是从现实的人世社会实际出发,把它们作为“修己安人”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提出、而阐明、而宣扬的。可是一到董仲舒手里就变了样。例如,所谓“五常”中的仁和义自然很重要,但是董仲舒不认为仁和义作为伦理德目是人类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而是天的产物、“天人感应”的产物。他的原话是:“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 董仲舒认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 延及群生也。”这里明明讲的是现实的人世问的问题,却偏要把它们蒙在一层厚厚的神奇古怪的天意黑幕中。
“王权神授”是天命所定。封建社会常常和迷信连在一起, 而迷信又常和愚昧连在一起,但利用愚昧进行迷信行为的人,却常常不是愚昧的而是颇有智慧的人。董仲舒编造出来的“王权神授”的奇谈怪论,就是属于这一类。董仲舒把所谓“天”打扮成为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的、主宰人间万事万物特别是人的祸福的、至高无上的有人格的神。神的意志就是天命。董仲舒首先利用他的所谓“天人合一”的论调,把天和人连结起来,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大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夏秋冬之类也。①请看,天不仅是人格神,而且成了人的“曾祖父” 了,而人的所有形体、血气、德行、好恶、喜怒都是天赋与的;甚至人的喜怒哀乐和春夏秋冬都密切相连,这种牵强附会的论调和孔子思想有什么共同点呢?可是,董仲舒虽然能够编造“天人合一”的把戏,但毕竟无法命令他捏造的“天”(即那位曾祖父)直接管人间的事,他还是必须叫人管人。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真正管人的是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作为人本身的王(或天子,或皇帝),他为了神化王权,只好说王是代天管人,是天人之中介, 并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又说“天子受命于天, 天下受命于天子“。于是,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自圆其说了。你看,君王、天子、皇帝都是受命于天来管理人间事的,这样“天”不是通过所谓君王、天子、皇帝而和人间结合起来了吗?这不就是董仲舒所谓的“天人合一”吗? 实质上,这不就是有意抬高封建帝王的无上权威,又通过不是神而是人(即封建帝王)来统治人、剥削人、压迫人,同时又使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人相信这是天命吗?这不就可以欺骗、迷惑一些人特别是愚昧无知的人俯首贴耳、甘心情愿无条件地服从“替天行道”的君王、天子、皇帝了吗?他甚至还用测字先生的方法来解释“王“字,说: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不仅如此,他还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地代天说教,似乎天是一心希望他的儿子(天子)要成为圣主,不要成为亡国之君,因而说:《春秋》之中,视前 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董仲舒所精心塑造起来的“天”对他的儿子,即人间的帝王天子,可谓宠爱备至,并以灾害、怪异等劝告之,以保其专制独裁的王位代代相传,董仲舒热衷于援引孔子的话以显示其儒者面貌,可是他恰恰忘掉了孔子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子不语怪、力、乱、神”。董仲舒对此不知作何感想?
3.“天下变,道亦不变”和“三正”、“三统”是天志所立。评价古人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看他比他的前人在思想上、学术上有所前进还是后退;第二个标准是用现代标准去看他,在他的思想学术中有哪些还有用处。因为研究古人对现代毫无用处,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最多只能当作古董;古董也有用处,但那是另外一种用处。根据以上两个标准来研究董仲舒提出的“天下变,道亦不变”和“三正”、“三统”的问题就明其真相了。什么叫“天不变,道亦不变”?先看董仲舒自己的解释:道之太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①董仲舒这里讲的道,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指包括政治、伦理、文化、教育等等在内的社会上层建筑。这本来都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是,董仲舒却避开现实问题,利用他的“天人感应”的论调,把这个所谓大道归之于“天”志所立(“原出于天”),这就把事实完全颠倒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颠倒呢?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明确人间的一切都是“天”安排的, 二是人间的封建贵族专制统治是永恒不变的,是天命,非人力所能改变。把董仲舒这段话和在他三百余年前孔子的一段话对照一下,问题就清楚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段话的缺点前已评析,这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加以引用。它明确指出,人间的礼义、人伦等“大道” 都是人在损益中发展的。孔子又说“人能弘道”,就是说,大道之弘扬在人,而他并没说在天。由此可见,用第一个标准来看,董仲舒比孔子倒退了多么远!至于用第二十标准来看,那就更清楚了。根据现代科学的论证,整个宇宙包括天在年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说它不变,在现代科学面前,实在幼稚可笑。因此,董仲舒除了作为古董和反面教员外还有什么意义呢!至于董仲舒编造出来为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调服务的所谓“三正”、“三统”,既无学术价值,又无实际意义。但仍有必要略作介绍,乃用以见董仲舒编造这番怪论的用心、何况历史上被其迷惑者也并非无人。所谓“三正”、“三统”,是董仲舒根据传说夏、商、周三代曾使用不同历法而牵强附会地编造出来的。夏、商、周三代分别用十二地支中的前三个即子、丑、寅三十月(分别为现代衣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正月岁首),夏代以寅月为岁首,这就叫建寅;殷代以丑月为岁首,这就叫建丑;周代以子月为岁首,这就叫建子;合称为“三正”。董仲舒认为, 由于子月“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这就叫“赤统”;丑月“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此殷“尚白”, 这就叫“白统”;寅月“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因此夏“尚黑”,这就叫“黑统”;合称“三统‘。他说这“三正”、“三统”是王朝兴废改制的标志,是不断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在董仲舒的眼里,历史就是在“三而复”的循环下永远踏步不前,王朝的兴废也仅仅是“改正朔”(“三正”不断循环使用)、“易服色”(黑、白、赤三种颜色即“三统”循环采用),而“若夫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这些正是表现封建专制社会本质的东西──作者),尽如故”④。所以董仲舒又坦率地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⑤一言以蔽之,由天命改朝换代时,封建社会的本质不能变动,封建专制君王的至上权威不能变动,所能改动的只是“改正朔”、“易服色”等表面文章。这就是董仲舒奇谈怪论的实质。中国封建社会延长如此之久,进步因素伸张如此之慢,董仲舒的上述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孔子儒家思想的分化和不同学派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统治者都竞相礼聘懂得《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的儒生,以便在政治、外交、日常生活等各方面为他们出谋划策以至帮忙和帮闲。因此,儒家学派有了很大发展。孔子弟子中有很多人在孔子死后也都开始收徒授业,于是孔门后学也就越来越多,对孔子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也越来越有差异。孔子弟子出身不同、阅历不同、造诣不同,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各执己见、各立门户,相互指责的情况屡见不鲜。从《论语》下述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子游日:“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未也。本①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 “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倦作传解──作者注) 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②这里子游、子夏所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是教门人弟子以“君子之道”先从何处人手的问题。子游批评子夏有末无本,或重末轻本,子夏不同意子游的责难,而认为哪个应该先教,哪个应该后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子夏的意见和孔子“因材施教”,“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等似较近。在《论语》等书中像这类相互指责的话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由于儒家内部观点不同、相互指责,逐步形成了一些打着孔子儒家招牌而相互对立的派别。《韩非子·显学》篇指出:“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 有孙氏(即荀卿──作者)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便是所谓儒家八派。此外,荀子也曾经批评过“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等等。在这些儒家派别之中,只有以祖述孔子为己任的孟轲和荀卿为代表的两派,在一定程度上对孔子思想既有所阐述,也有所补充。发展和修正。如孟子在君民关系上,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一“民贵君轻”思想不仅大大发展了孔子思想,而且是在封建社会中敢于提出的民主思想的可贵萌芽。在君臣关系上,主张相互尊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特别提出道德高于王权,王者必以大人为师的观点, 他说:“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 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他甚至认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对孔子“忠君尊王”思想的重大修正和发展,十分可贵。这些言论曾引起一些专制暴君的反感,例如朱元璋就曾命令御用文人删除这一类文字,甚至企图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子游这里讲的“本”主要是指仁、礼等而言。荀子在“隆礼”的基础上既重视利,也重视义,一面强调努力耕战以加强国家实力,一面又强调推行王道以争取民心。他说:“传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这些思想既没有孔孟仁义礼乐的迂远疏阔,也避免了法家严刑峻法的残刻寡恩,集中两者的优点,为地主阶级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礼治理论。荀子的学生李斯、韩非把他的学说运用于秦国,使秦完成统一大业;但他们片面地发展了荀子思想,提出专任法、术、势的法家理论,导致了秦朝的速亡。为了论证自己的礼治思想,荀子提出新的天道观,认为天即是自然,它有自己运动的规律,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 让自然为人类服务。他还提出“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抗,由性恶强调礼法的规范作用和对人进行教育的必要性。其实,孟子主张性善, 荀子主张性恶,两人都是各执一端,都不符合孔子提倡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精神。可以看出,孔子在性善、性恶这个问题上站得更高,看得更深,因为对任何人来讲,性善或性恶都不是天生的,善和恶归根到底决定于后天环境和教育。由此可见,当时孔子儒家思想这两大学派,其中孟子除了对孔子思想有一定补充和发展外,更多的是遵循孔子思想的基本原则;而荀子除了遵循孔子思想主要原则外,更多的则是对之有所补充、有所修正、有所发展。这是孔子思想分化和建立不同学派的开始,而以后的分化和学派的建立陆续发生,其中包括两次对孔子思想的大篡改。
第二,“独尊儒术”和对原始孔子思想的第一次大篡改历史是常常以讽刺性的戏剧形式出现的。向汉武帝提出并被接受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是“为儒者宗”的今文经学派儒者董仲舒,而第一次大篡改孔子思想的也正是这位董仲舒。董仲舒对原始孔子思想的大篡改, 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问题上:
1.“三纲”、“五常”是天意所决。前已指出,孔子一贯主张的“忠君尊王”思想是维持和巩固封建君主宗法统治的思想支柱,这是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同时也是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产物,但这里并没有天命神鬼这类的话夹杂其间。孔子思想中的君臣、君民关系还保留着一定的君臣、君民相互尊重的原始民主精神,而这一精神则完全被董仲舒糟踏和篡改了。董仲舒把当时人间最重要、最普遍的三种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所谓“三纲”,这完全是一方绝对顺从另一方的主奴关系。为了证明“三纲”是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董仲舒又请出天来助长声势,他说:“王道之三纲, 可求于天。”这样,董仲舒就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三纲”是天意所定, 不允许人作任何改变,用天意把这三种关系纳入极端封建专制的框子里去了。在这“三纲”中,君臣关系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纲,他明目张胆地说: “《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②并以天的名义宣布“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即君王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君臣的关系是如此,父子、夫妇关系也类此。这种阴森森的“三纲” 关系不是对孔子前面所提出的君臣关系中一些原始民主精神和父慈子孝、夫
义妇听的父子、夫妇和顺关系的歪曲和篡改吗!董仲舒生于孔子死后三百余年,这期间科学文化和社会经济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他对自然、对天的了解理应比孔子要多些,理应比孔子思想有所前进,但实际上却比孔子还大大倒退了。例如对于“天”,孔子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很少谈天,而董仲舒则大谈其“天人感应“,并且认为“三纲”乃天意所决。这难道不是董仲舒异想天开、随心所欲地篡改孔子思想而强不知以为知地妄谈“天”吗! 董仲舒的所谓“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前四个仁、义、礼、智原是孟子所讲的四德,董仲舒为了符合神秘的五行之说,加上一个信。其实,如前所说,仁、义、礼、智、信都是孔子仁的人生哲学中的部分德目, 孔子完全是从现实的人世社会实际出发,把它们作为“修己安人”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提出、而阐明、而宣扬的。可是一到董仲舒手里就变了样。例如,所谓“五常”中的仁和义自然很重要,但是董仲舒不认为仁和义作为伦理德目是人类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而是天的产物、“天人感应”的产物。他的原话是:“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 董仲舒认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 延及群生也。”这里明明讲的是现实的人世问的问题,却偏要把它们蒙在一层厚厚的神奇古怪的天意黑幕中。
“王权神授”是天命所定。封建社会常常和迷信连在一起, 而迷信又常和愚昧连在一起,但利用愚昧进行迷信行为的人,却常常不是愚昧的而是颇有智慧的人。董仲舒编造出来的“王权神授”的奇谈怪论,就是属于这一类。董仲舒把所谓“天”打扮成为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的、主宰人间万事万物特别是人的祸福的、至高无上的有人格的神。神的意志就是天命。董仲舒首先利用他的所谓“天人合一”的论调,把天和人连结起来,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大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夏秋冬之类也。①请看,天不仅是人格神,而且成了人的“曾祖父” 了,而人的所有形体、血气、德行、好恶、喜怒都是天赋与的;甚至人的喜怒哀乐和春夏秋冬都密切相连,这种牵强附会的论调和孔子思想有什么共同点呢?可是,董仲舒虽然能够编造“天人合一”的把戏,但毕竟无法命令他捏造的“天”(即那位曾祖父)直接管人间的事,他还是必须叫人管人。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真正管人的是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作为人本身的王(或天子,或皇帝),他为了神化王权,只好说王是代天管人,是天人之中介, 并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又说“天子受命于天, 天下受命于天子“。于是,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自圆其说了。你看,君王、天子、皇帝都是受命于天来管理人间事的,这样“天”不是通过所谓君王、天子、皇帝而和人间结合起来了吗?这不就是董仲舒所谓的“天人合一”吗? 实质上,这不就是有意抬高封建帝王的无上权威,又通过不是神而是人(即封建帝王)来统治人、剥削人、压迫人,同时又使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人相信这是天命吗?这不就可以欺骗、迷惑一些人特别是愚昧无知的人俯首贴耳、甘心情愿无条件地服从“替天行道”的君王、天子、皇帝了吗?他甚至还用测字先生的方法来解释“王“字,说: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不仅如此,他还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地代天说教,似乎天是一心希望他的儿子(天子)要成为圣主,不要成为亡国之君,因而说:《春秋》之中,视前 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董仲舒所精心塑造起来的“天”对他的儿子,即人间的帝王天子,可谓宠爱备至,并以灾害、怪异等劝告之,以保其专制独裁的王位代代相传,董仲舒热衷于援引孔子的话以显示其儒者面貌,可是他恰恰忘掉了孔子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子不语怪、力、乱、神”。董仲舒对此不知作何感想?
3.“天下变,道亦不变”和“三正”、“三统”是天志所立。评价古人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看他比他的前人在思想上、学术上有所前进还是后退;第二个标准是用现代标准去看他,在他的思想学术中有哪些还有用处。因为研究古人对现代毫无用处,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最多只能当作古董;古董也有用处,但那是另外一种用处。根据以上两个标准来研究董仲舒提出的“天下变,道亦不变”和“三正”、“三统”的问题就明其真相了。什么叫“天不变,道亦不变”?先看董仲舒自己的解释:道之太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①董仲舒这里讲的道,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指包括政治、伦理、文化、教育等等在内的社会上层建筑。这本来都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是,董仲舒却避开现实问题,利用他的“天人感应”的论调,把这个所谓大道归之于“天”志所立(“原出于天”),这就把事实完全颠倒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颠倒呢?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明确人间的一切都是“天”安排的, 二是人间的封建贵族专制统治是永恒不变的,是天命,非人力所能改变。把董仲舒这段话和在他三百余年前孔子的一段话对照一下,问题就清楚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段话的缺点前已评析,这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加以引用。它明确指出,人间的礼义、人伦等“大道” 都是人在损益中发展的。孔子又说“人能弘道”,就是说,大道之弘扬在人,而他并没说在天。由此可见,用第一个标准来看,董仲舒比孔子倒退了多么远!至于用第二十标准来看,那就更清楚了。根据现代科学的论证,整个宇宙包括天在年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说它不变,在现代科学面前,实在幼稚可笑。因此,董仲舒除了作为古董和反面教员外还有什么意义呢!至于董仲舒编造出来为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调服务的所谓“三正”、“三统”,既无学术价值,又无实际意义。但仍有必要略作介绍,乃用以见董仲舒编造这番怪论的用心、何况历史上被其迷惑者也并非无人。所谓“三正”、“三统”,是董仲舒根据传说夏、商、周三代曾使用不同历法而牵强附会地编造出来的。夏、商、周三代分别用十二地支中的前三个即子、丑、寅三十月(分别为现代衣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正月岁首),夏代以寅月为岁首,这就叫建寅;殷代以丑月为岁首,这就叫建丑;周代以子月为岁首,这就叫建子;合称为“三正”。董仲舒认为, 由于子月“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这就叫“赤统”;丑月“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此殷“尚白”, 这就叫“白统”;寅月“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因此夏“尚黑”,这就叫“黑统”;合称“三统‘。他说这“三正”、“三统”是王朝兴废改制的标志,是不断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在董仲舒的眼里,历史就是在“三而复”的循环下永远踏步不前,王朝的兴废也仅仅是“改正朔”(“三正”不断循环使用)、“易服色”(黑、白、赤三种颜色即“三统”循环采用),而“若夫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这些正是表现封建专制社会本质的东西──作者),尽如故”④。所以董仲舒又坦率地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⑤一言以蔽之,由天命改朝换代时,封建社会的本质不能变动,封建专制君王的至上权威不能变动,所能改动的只是“改正朔”、“易服色”等表面文章。这就是董仲舒奇谈怪论的实质。中国封建社会延长如此之久,进步因素伸张如此之慢,董仲舒的上述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无其他回答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