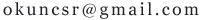斜坡巷的杜利先生死了,这对我爸爸是个可怕的打击。杜利先生是位流动销货员,自己有小汽车,两个儿子上的都是多米尼克教会学校。论社会地位,他要比我们高出十万八千丈,但从来不摆臭架子。杜利先生是个知识分子,也象所有的读书人一样,他最喜欢的就是聊天;而爸爸呢,还勉强算得上读过好些书,能够欣赏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杜利先生真是个了不起的聪明人。他做生意交游很广,与宗教界又常有接触,所以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几乎没有不清楚的。他夜夜从街那边走到我们家来,对我父亲大谈新闻背后的新闻。他嗓门低低的,很诱人,脸上常带着聪颖的笑容。爸爸总是惊讶地倾听,不时也说几句引他住下讲。爸爸还会得意洋洋地插上这么一句,满面生辉地问我母亲:“你知道杜利先生要告诉我什么事吗?”直到今天,每逢有人向我传播什么小道消息,我还总是想问:“是不是杜利先生告诉你的?”
直到我亲眼看见他穿着褐色的寿衣躺在那里,蜡黄的手指上缠着念珠,我还是不能把噩耗当真。我总还觉得其中有诈,说不定哪一个夏日的黄昏,杜利先生又会在我家门口出现,向我们大揭阴间黑幕。可是爸爸却很难过,这既因为杜利先生与他年龄相仿,他的死难免叫爸爸担心什么时候也轮到自己,也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人会把市政当局肮脏的内幕新闻告诉他了。我们布拉尼巷里,象杜利先生一样读报的居民屈指可数,而且他们都不忽略这一事实:我爸爸只是个干力气活的。就连沙利文木匠,虽然他压根儿算不了老几,也自认比爸爸高出一头。因此,杜利先生的死的确非同小可。
“两点半到达克拉公墓。”爸爸若有所思地放下了报纸。
“你该不是要去参加葬礼吧?”妈妈发慌了。
“这也该料得到的。”爸爸已察觉到妈妈反对的意思,“我可不能让人说闲话。”
妈妈按捺着性子说:“我看你去不去送葬,在别人眼里,不过和你送不送他上殡仪馆一样罢了。”
(当然罗,“上殡仪馆”是另一回事,因为送尸体上殡仪馆是下工后的事,而送葬却意味着少挣半天工钱。)
“那些人又差多全都不认识我们。”她又补上一句。
“上帝保佑我们,”父亲庄严地回答,“要轮到我们自己,也会希望人家来的。”
平心而论,为了老邻居,爸爸从来都是舍得放弃半天的收入的。主要的原因倒不是他喜欢葬礼,而是他是个讲良心的人,他希望别人怎么待自己,也就怎么去待别人;他一想到日后自己死了,别人也一定会为他举行体面的葬礼,就感到莫大的安慰。不过,也得为妈妈说句公道话,她倒不是吝啬半天的收入,这好歹我们总还算大方得起。
你要知道,爸爸有个大毛病——酗酒。他可以强忍住,几个月甚至几年,滴酒不沾。这种时候他可真象金子打成的好人。早上他总是头一个起来,烧好茶端一杯到妈妈床头,晚上也总是呆在家里读报;他用省下的钱买了一套崭新的蓝哔叽衣服,还有顶圆顶呢帽。他讥笑那些酒鬼笨蛋,一星期一星期把挣来的血汗钱送进酒店老板的腰包;有时候,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他还拿出纸笔,精确地计算一番,看看当一个禁酒主义者每周能省下多少钱。由于天性乐观,有时他还会把可能的寿命也计算在内,得出的总数叫人兴奋得喘不过气来。到他归天之时,会有好几百镑呢!
我似乎只知道,这是个不详之兆,说明他心里的骄傲情绪已经膨胀,他自认为要比邻居们强。迟早这种情绪会膨胀到非要发泄不可的地步,一定得庆祝一番才甘休。于是乎他就来上一杯——当然不是威士忌,不是诸如此类的烈酒——只是黑啤酒之类温和无害的饮料。可这一来就糟了。第一杯刚下肚,他就意识到自己当了傻瓜,要用第二杯来洗刷这耻辱的记忆,没用,又干上第三杯……最后回家的时候,他已经醉得踉踉跄跄的了。正如劝人为善的印刷品上所说,从此开始了“醉汉发展过程”。第二天他总是头晕得没法上工,只好让妈妈去替他请假。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会又变得可怜、粗野、沮丧。他一旦喝开了头,就会一个劲喝下去,直到连厨房里那座时钟也喝光。妈妈和我太熟悉这一切了,所以对所有能挑逗他酗酒的危险机会都怕得要命。葬礼,也是这种机会之一。
“我得上邓菲那儿去干半天活,”妈妈忧心忡忡地说,“可谁来照管拉里呢?”
“让我来吧,”爸爸和蔼地说,“走动一下对他也有好处。”
用不着多说,大家都明白,我才用不着别人照看,要让我留在家,我还能把索尼照料得好好的呢。要我跟父亲一道,是想让我充当他的制动器。尽管我这个制动器从来不灵,但妈妈还是认定我行。
第二天,我刚放学回来,爸爸已在家里。他替我和他煮了一盅茶。他煮茶是好手,但干别的手脚都太笨;他切面包的那个样子简直叫人打战。喝过茶,我们就走下斜坡上教堂去。爸爸穿着他最好的那套蓝哔叽,圆顶呢帽斜戴在头上,有点风流哥儿的味道。他在来送葬的人当中,发现了彼得·克劳利,真是高兴极了。彼得也是个危险信号,凭以往星期日早弥撒后的经验,我早就懂得这一点。就象妈说的,他是坏人,他参加葬礼只为了不花钱白喝酒。事实上他根本就不认识杜利先生!爸爸也有点瞧不起他,认为他还不如那些把血汗钱花在酒店里的笨蛋,因为他喝酒差不多从不自己掏腰包!
在爸爸看来,这葬礼够气派的。我们还没出发,还没冒着午后的阳光,跟在灵车后面朝墓地走去,他已经把一切都调查得一清二楚了。
“五辆马车!”他报道说,“五辆马车,十六辆蓬车!一位市府参事,两名地方议员,还有不计其数的教士。自从酒店老板威利·麦克死后,我还没见过谁的葬礼有这种排场。”
“这自然罗,他人缘好呀。”克劳利的沙哑嗓门响了。
“我的天,还用你来告诉我?”父亲尖声说,“难道他不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他去世前两天——仅仅两天哇——他那天晚上还到我家来着,把住宅合同的情况告诉我。市政府那些人全是强盗。不过,就连我也没料到他结交有这么广。”
爸爸快步朝前走,兴奋得象个小孩,周围的一切都叫他感兴趣:送葬者、山迪威尔路上的漂亮房屋。最危险的信号全出现了:阳光灿烂的天气,气派十足的葬礼,僧俗两方面的大人物。这一切都在挑逗、刺激,让父亲暴露出天性中虚荣、轻浮的一面。眼看他的老友被送进墓穴,他内心产生了一种类似欢愉的感觉,有种尽了义务的轻松感,而且也不无庆幸,不管以后在漫长的夏日黄昏,他会如何强烈怀念可怜的杜利先生,但毕竟是他想杜利,而不是杜利怀念他。
“咱们在人散前走吧。”爸爸悄悄对克劳利说,这时掘墓人才刚向穴里撒下第一锹土。父亲离开了墓地,蹦蹦跳跳的,活象头从一个草墩跳到另一个草墩的山羊。那些马车夫,虽然不象爸爸那样已经几个月没喝酒了,但瘾头似乎也不比他小,他们都满怀希望地抬头张望。
“那边快完事了吧,米克?”一位马车夫大声问道。
“快了,只剩下最后的祈祷啦!”听父亲说话那调门,活象在宣布什么特大喜讯。
离酒店还有几百码,马车队卷着尘龙超过了我们。虽然天气一热,爸爸腿就不灵便,但他还是加快了步子,还一面紧张地回头,看看大队的送葬者是否翻过岭来了。人群一到,你就可能要等啦。
我们到达酒店时,那些马车早已排成一行停在店外。系着黑领带、神气庄严的先生们正小心安慰那些神秘的女士,她们很庄重,只从放下的马车遮帘后伸出手来。酒店里只有马车夫和两个骚婆娘。我想,是刹车的时候了,于是就扯扯爸爸的衣角。
“爹,咱们现在就回家不好吗?”
“只等两分钟,”他满脸堆笑,十分亲切地说,“喝完一瓶柠檬水就走。”
这叫收买拉拢,我明白,但我一向是个意志薄弱的孩子。爸爸要了一瓶柠檬水和两品脱啤酒。我口很渴,一下就喝光了我的那份。爸爸可不象我,他几个月没喝过酒了,眼下可要慢慢地仔细地享受这无穷无尽的乐趣。他掏出烟斗,吹气通了通,装上烟丝,辟辟啪啪地划了几声火柴来点烟,他拼命吸着,眼珠都凸出来了。然后,他不慌不忙地转过身,背朝酒柜,一只胳膊肘支在柜台上,好象根本就不知道背后还有酒,慢条斯理地刷掉手掌上的烟末。他已安心要呆到天黑,从容不迫地逐一讲起他所参加过的盛大葬礼。马车全走了,那些次要的送葬者也拥进来了,店里已经半满。
“爹,”我又扯扯他的衣裳,“咱们回去吧。”
“呃,你妈还要过很久才能回家。”他说得还挺好听,“到外面马路上玩去,好不好?”
但我一听就知道是扯淡。一个人孤零零的,怎么能在陌生的街道玩儿呢?和以往一样,我很快就厌倦了。我知道爸爸挺能挨,非到天黑他是不会走的。我明白,恐怕我得领他回家了,他会醉得一塌糊涂,布拉尼巷的老女人们会全都跑到门口看笑话,说什么,“瞧,米克·德莱尼又醉啦。”我还知道,妈会着急得半疯,生怕爸爸第二天上不了工,这星期还没过完,她就得把那钟用披肩盖住,朝当铺里跑。厨房里要没个钟,静悄悄的,我怎么也习惯不了。
我的口还是渴。我发觉只要踮起脚尖,就够得着爸爸的酒杯。一个念头在我脑里一闪:试试杯里东西是啥滋味可是怪有趣的。爸爸背朝酒杯,是不会发现的。我拿下酒杯,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真扫兴。我真不明白他怎么能喝得下这种玩意。看来他是从来没沾过柠檬水的吧。
我本想劝他改喝柠檬水,可他正在一本正经地高谈阔论。他说,乐队是葬礼一个重要的附加成分。他摆出一副姿势,象倒持着一支步枪,哼了几节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克劳利敬佩得直点头。我又喝了一大口,马上就领略了黑啤酒的妙处。我觉得精神兴奋,心情开明而且达观。爸爸又哼了几节《扫罗》里的《死亡进行曲》。这酒店是个好地方,这葬礼也真够排场,我相信可怜的杜利先生在天之灵一定十分满意。同时我还想,他们可能也给他一个乐队。就象爸爸说的,乐队是重要的附加成分呀。
啤酒的妙处还在后头呢。它能叫你超脱自身躯壳,或者说使你飘飘然,就象腾云驾雾的六翼天使,在一旁观看你自己的模样。瞧你,两腿交叉,斜靠酒柜,超脱了琐事的烦扰,成人般思索深邃、严肃、有关生与死的问题。看着自己的模样,想想多滑稽,你一定会突然觉得很窘,总想咯咯笑出声来。可是,等我把一杯全喝完,这种状态也完结了;我发觉要把酒杯放回原处很困难,柜台象长高了不少。我的忧郁症又复发了。
“是啊,”爸爸一面向后伸手去拿酒杯,一面虔诚地说,“不论他在天堂还是地狱,愿上帝让这可怜人的灵魂安息!”他打住了,先瞧瞧杯子,又望望周围的人。“喂,”听他声音还挺和气,他还当是别人和他恶作剧呢,“谁干的好事?”
谁也没吭声,酒店掌柜和那两位老女人先看看爸爸,又望望他的酒杯。
“谁也没喝你的酒,我的好人。”一位女人忿忿不平地说,“你当我们是贼?”
“呃,米克,这儿是没人会干这种勾当的呀。”听口气掌柜也很惊讶。
“哼,是有人把我的酒偷了。”爸爸脸上的笑容消散了。
“真要有人喝,也只能是你身边的人干的。”那女人阴阳怪气地说,还狠狠地扫了我一眼。爸爸马上恍然大悟。我想当时我一定是醉眼乜斜的了。爸爸弯下腰,摇着我。
“你没事吧,拉里?”他大惊失色。
彼得·克劳利低头朝我呲牙直笑。
“怎么能叫人相信这种事?”
我能,而且毫无困难。我要呕吐了。爸爸生怕弄脏他那套好衣服,吓得往后一跳,连忙打开后门。
“快跑!快!快!”他喊道。
门口对面有堵攀满常青藤的墙,阳光正照在它上面。我拔腿就朝外冲。我的动机本来很好,可动作却过火了,因为我一扑,和墙壁撞了个正着,我心想,它该让我撞得够疼的了。我素来很讲礼貌,所以在和它碰第二次前,还说了声“对不起”。爸爸还是担心他那套衣服,他走到我背后,在我呕吐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扶住我。
“好孩子!”他鼓励道,“吐了就舒服了。”
天啊,我可不舒服,怎么也谈不上舒服。我一点也不顾他的面子,哇哇大哭起来,他领我回到店里,让我坐在那两位骚女人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她们愤慨地挺直身板,还在生父亲的气,怨他错怪了她们。
“老天爷啊!”一个女人呻吟般叫道,怜悯地望着我,“这德行,配做父亲么?”
“米克,”掌柜的慌张地说,他正朝我留下的污迹撤锯屑,“这里可不是孩子呆的地方。趁警察没发现,你最好赶快带他回家去吧。”
“仁慈的天父阿!”爸爸抽抽噎噎地说。他翻眼看天,无声地击掌,只有在六神无主的时候,他才有这副模样。“我倒了什么霉哟!他妈会怎么说啊?……女人就该呆在家里照管自己的孩子!”他咆哮着补上一句,显然是冲着那两个骚娘们说的,“马车全走了吗,比尔?”
“早走完了,米克。”酒店掌柜回答。
“那我领他回去吧。”爸爸垂头丧气地说,“我再也不带你出来了,”他恐吓我。“给,”他从胸袋掏出一根干净手帕,“按住你的眉棱。”
看见手帕上的血迹,我才知道自己的头破了。我的太阳穴马上砰砰直跳,我又嚎哭起来。
“嘘!别!别!”爸爸烦躁地说,领我出了店门,“人家还当你撞死了呢!这不要紧嘛,到家洗洗就好啦。”
“坚强些,老伙计!”走在我另一边的克劳利安慰道,“一会就没事啦。”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两个人,他们根本就不懂喝了酒会怎样。我一遇风,又被太阳一晒,酒力发作得更厉害了。我踉踉跄跄,摇摇晃晃,就象在风头浪尖上颠簸一样。爸爸又抽抽噎噎的了。
“全能的上帝啊!全街人都出来了!我怎么老是这么例霉!你就不能走好些吗?”
我走不好。但我看得一清二楚。布拉尼巷的娘儿们,不论老少,全让阳光引出来了。她们有的靠着矮门,有的坐在门槛上,现在全都停止饶舌,张开嘴巴观看眼前的怪事:两位毫无醉态的中年人,带着一个眉棱上开了道口子的、醉醺醺的小男孩回家。爸爸左右为难,一方面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快些让我藏进家里,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有必要解释一番,申明不是他的过错。后来,我们在罗奇太太的屋前停下了。街对面一家门前聚集着一群老太婆,我一看就讨厌,看样子她们对我全都太感兴趣了。我斜靠着罗奇太大家的墙壁,双手插在裤兜里,满怀伤感,怀念起可怜的杜利先生,他躺在克拉公墓冰冷的坑里,再也不能在这街道上迈步。我越想越动感情,就唱起了一首父亲最喜欢的歌。
墓穴冷冰冰,见不了明诺尼亚,也回不了钦科拉。
“唉,可怜的孩子!”罗奇太太叹道,“他的嗓子可不挺好的嘛,上帝保佑他吧!”
我也自认如此,爸爸却举起一根手指威胁我:“别嚷了!”这就叫我觉得真是咄咄怪事。也许是他还没意识到现在唱这支歌是正当其时吧,于是我就唱得更响了。
“住口,我叫你住口,”他尖声嚷道,接着又朝罗奇太太挤出一笑,“我们快到家了。让我抱你走吧。”
尽管我醉成了这样子,还不至于胡涂到这么丢脸,让人给抱回家。
“得了,”我声色俱厉,“你别打扰我好不好?我好好的,能走。只是我的头有点晕。只要歇一会就好的。”
“要歇就回家上床歇去。”他恶狠狠地说,想把我抱起来,看他满面通红,我知道他发火了。
“上帝呀,”我蛮横地说,“回家干什么?你他妈的就不能别管我?”
不知道为什么,对面街上那群老太婆觉得这很逗趣,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想到你喝上一滴酒左邻右舍就全都来笑你,我气得肚皮都快炸了。
“你们笑谁?”我吆喝,朝她们攥拳头,“再不让开我就打肿你们的脸,叫你们笑笑自个儿。”
她们却觉得更好笑了;我可从来没遇见过这么没教养的人。
“滚开,你们这帮脏母狗!”我咒骂。
“住口,住口!你给我住口!”爸爸收起强装出的好脸,咆哮了。他抓住我的手臂,抱着我就走。婆娘们的尖笑气得我发狂,爸爸的威胁气得我发疯。我拼命想站定不动,但力气小,哪里拗得过他,只好扭过头来朝那帮女人瞪眼睛。
“小心些,不然回头我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我叫骂道,“我要教训教训你们,叫你们懂得给体面人让路。你们该呆在家里,洗干净你们的脏脸。”
“马上全街人都传遍了,”爸爸抽抽噎噎地说,“不干了,再也不干了,哪怕能活一千岁我也不干了!”
直到今天我都还不清楚,当时他到底是发誓不再带我出门,还是说不再喝酒了。他把我拖进家里,为了显示我的英雄气慨,我嚷起了《韦克斯福德少年》这首歌。克劳利知道他留下会有麻烦,便溜了。爸爸替我脱了衣服,把我弄到床上,但我却睡不着,只觉得天旋地转,难受极了。我又吐了,爸爸弄了块湿布进来替我擦地板。我浑身发烫地躺着,只听见他劈柴生火,后来又摆弄餐桌。
突然,砰的一声,大门撞开了,妈抱着索尼一阵狂风似地冲了进来,她平素和蔼温顺的样子全没有了,换上了一副暴跳如雷的凶相。显然,邻居把什么都告诉她了。
“米克·德莱尼,”她歇斯底里地叫道,“你把我的儿子怎么啦?”
“嘘,女人,嘘!嘘!”爸爸连嘘了几声,左脚换右脚地蹦跳,“你想让全街人都听见?”
“哈,”妈发出吓人的怪笑,“街上的人早知道喽。谁还不知道?你和那头畜生为了寻开心,竟拿黄汤灌我倒霉的儿子。他好端端的犯了你们什么啦?”
“我可没给他酒呀!”他高声辩白,邻人对这倒霉事可怕的曲解叫他不胜惊骇,“趁我转过背去,他把酒喝了。天啊,妈的你把我都看成什么人啦?”
“哼,”妈尖刻地回答,“什么人,现在谁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上帝饶恕你吧,把咱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那几个血汗钱花去喝酒还不算,还想带坏儿子,让他也变成和你一样游手好闲的酒鬼。”
说罢她走进房里,在我床边跪下。看见我眉棱上的伤口,她不禁迸出呻吟。厨房里,索尼哇哇大哭了。一会儿,爸爸出现在房门口,他的帽子遮住眼睛,满脸自我怜悯的神情。
“好哇,我已经够倒霉的了,你还要这样责怪我,”他埋怨,“我一整天没沾过一滴酒。他都喝光了我还喝啥?要说可怜,该算我呢,白白花费一天,还要在满街人面前丢人现眼。”
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后就老老实实提着饭盒上工去了。他一走,妈妈就扑到我床边吻我。好象这全是我的功劳。她还要替我请假,等到我眼睛好些了才上学。
“我的小勇士!”她的眼睛发亮,“是上帝让你去的。你是他的守护天使。”
讨 论
在这个滑稽故事里,人物的位置颠倒了。成了家庭丑闻,引起邻居非议讥笑的事情不是父亲醉倒街头,年幼的儿子吓怕了,可怜巴巴地想把父亲领回家,不让他在众人面前丢丑。倒是小孩子醉步蹒跚,走腔走调大唱其歌,还咒骂女邻居是“脏母狗”,弄得父亲六神无主,心慌意乱。如果这故事只是简单地给我们讲述这颠倒离奇的情节,而且到此为止,那么,充 其量它也只能算一个博人一笑而已的笑话。它就不怎么象篇小说,甚至还算不上好笑话。因为隽永的笑话,也必须扎根于对人性的真正理解之中。
在这故事里,父子位置的颠倒不是一时之技。只要我们稍加追溯,就可以发现这种颠倒是贯串整个故事的。在对待父亲酗酒毛病的大事上,拉里这孩子接受了母亲的观点。他象个大人,关心家庭的利益,但同时还必须提防自己孩子气的弱点。拉里忧心忡忡,知道什么是坏“兆头”。他太熟悉父亲一开酒戒就会发生什么后果。他一直很关心父亲,直到啤酒对他起了作用,他的忧虑才头一次消失。
在故事里,倒是父亲有种孩童般的天真坦白,这种性格常常还很讨人喜欢。想想他参加葬礼时的高兴劲吧:“在爸爸看来这场葬礼够气派的。”他报道说有“五辆马车,十六辆篷车!”后来,拉里又说他,“眼看他的老友被送进墓穴,他内心产生了一种类似欢愉的感觉,有种尽了义务的轻松感,而且也不无庆幸,不管以后在漫长的夏日黄昏,他会如何强烈怀念可怜的杜利先生,但毕竟是他想杜利,而不是杜利怀念他。”后来,他告诉那些等着上酒店的马车夫,说下葬仪式快结束了:“‘快了,只剩下最后的祈祷啦!’听父亲说话那调门,活象在宣布什么特大喜讯。”而几分钟后,他进了酒店,准备开酒戒、解长渴的时候,更别提他有多高兴了!
如果拉里的父亲稍有些心计,或者稍为自觉,这种幽默的韵味就会失去,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对他就会采取另外一种态度了。他因为单纯天真闯了祸,也因为单纯天真获得读者谅解。与其说他有罪,还不如说他受罪——由于邻居婆娘们“可怕的曲解”,说他灌醉了自己的儿子,使他受到妻子责骂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显得突出。这位父亲的性格,不但与故事本质的意义有密切的关系,甚至还能决定我们认为这故事是不是真有趣的看法。尽管“一切情况都说明他不对”,他还是有种受到伤害的无辜的感觉。
人物位置大致颠倒的最逗笑的例子,就是在从酒店回家的路上,父亲并没有强迫叫叫嚷嚷、醉态蹒跚的儿子住口,而是哀求他清醒些,别嚷了——照常理推测,如果喝醉的是父亲,拉里也会这样对待父亲的。然而,这种颠倒逗笑的主要根源,却出自父亲的性格:如果他是个残酷野蛮的人,就会强迫儿子闭嘴。而这样父子就不会有什么逗人发笑的事了,一强迫,一粗暴,也放无幽默可言了。
这种颠倒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是在故事的末尾(也是故事的高潮),小孩子的淘气被曲解为神的安排,醉醺醺、摇摇晃晃在大街上出丑的小男孩,在母亲眼里却成了引导意志薄弱的父亲走正道的“守护天使”。我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笑——她赞扬拉里的说法,简直荒唐得象马拉柏洛柏太太①一样令人吃惊——不过,从她的观点来看,她的话也有相当道理:拉里成了小“男子汉”了。他使她少跑了一次常上的当铺。
1.拉里偷喝父亲啤酒这件事写得合情合理吗?拉里是否常干这类事?拉里父亲把酒搁在背后,让儿于喝光了都还不知道,这事可信吗?
2.作为一个孩子,拉里对他父亲的观察是否太成熟了?这故事是拉里事后不久就写的呢,还是隔了许多年,他成人后才写的?
3.这篇小说,情况的交待安排得很有技巧。请试加评论。迟迟不点出拉里父亲好酒,这样有什么好处?
4.拉里眉棱裂了个口子,这有什么重要意义?伤口和鲜血是否能为这意外事件增添某种反响?
5。是什么因素使得这故事不光是个笑话?如果你在答案中使用了“塑造人物”这术语,请解释你的意思。
①谢立丹的喜剧《竞争者》中的人物,以误用文字著名。
直到我亲眼看见他穿着褐色的寿衣躺在那里,蜡黄的手指上缠着念珠,我还是不能把噩耗当真。我总还觉得其中有诈,说不定哪一个夏日的黄昏,杜利先生又会在我家门口出现,向我们大揭阴间黑幕。可是爸爸却很难过,这既因为杜利先生与他年龄相仿,他的死难免叫爸爸担心什么时候也轮到自己,也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人会把市政当局肮脏的内幕新闻告诉他了。我们布拉尼巷里,象杜利先生一样读报的居民屈指可数,而且他们都不忽略这一事实:我爸爸只是个干力气活的。就连沙利文木匠,虽然他压根儿算不了老几,也自认比爸爸高出一头。因此,杜利先生的死的确非同小可。
“两点半到达克拉公墓。”爸爸若有所思地放下了报纸。
“你该不是要去参加葬礼吧?”妈妈发慌了。
“这也该料得到的。”爸爸已察觉到妈妈反对的意思,“我可不能让人说闲话。”
妈妈按捺着性子说:“我看你去不去送葬,在别人眼里,不过和你送不送他上殡仪馆一样罢了。”
(当然罗,“上殡仪馆”是另一回事,因为送尸体上殡仪馆是下工后的事,而送葬却意味着少挣半天工钱。)
“那些人又差多全都不认识我们。”她又补上一句。
“上帝保佑我们,”父亲庄严地回答,“要轮到我们自己,也会希望人家来的。”
平心而论,为了老邻居,爸爸从来都是舍得放弃半天的收入的。主要的原因倒不是他喜欢葬礼,而是他是个讲良心的人,他希望别人怎么待自己,也就怎么去待别人;他一想到日后自己死了,别人也一定会为他举行体面的葬礼,就感到莫大的安慰。不过,也得为妈妈说句公道话,她倒不是吝啬半天的收入,这好歹我们总还算大方得起。
你要知道,爸爸有个大毛病——酗酒。他可以强忍住,几个月甚至几年,滴酒不沾。这种时候他可真象金子打成的好人。早上他总是头一个起来,烧好茶端一杯到妈妈床头,晚上也总是呆在家里读报;他用省下的钱买了一套崭新的蓝哔叽衣服,还有顶圆顶呢帽。他讥笑那些酒鬼笨蛋,一星期一星期把挣来的血汗钱送进酒店老板的腰包;有时候,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他还拿出纸笔,精确地计算一番,看看当一个禁酒主义者每周能省下多少钱。由于天性乐观,有时他还会把可能的寿命也计算在内,得出的总数叫人兴奋得喘不过气来。到他归天之时,会有好几百镑呢!
我似乎只知道,这是个不详之兆,说明他心里的骄傲情绪已经膨胀,他自认为要比邻居们强。迟早这种情绪会膨胀到非要发泄不可的地步,一定得庆祝一番才甘休。于是乎他就来上一杯——当然不是威士忌,不是诸如此类的烈酒——只是黑啤酒之类温和无害的饮料。可这一来就糟了。第一杯刚下肚,他就意识到自己当了傻瓜,要用第二杯来洗刷这耻辱的记忆,没用,又干上第三杯……最后回家的时候,他已经醉得踉踉跄跄的了。正如劝人为善的印刷品上所说,从此开始了“醉汉发展过程”。第二天他总是头晕得没法上工,只好让妈妈去替他请假。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会又变得可怜、粗野、沮丧。他一旦喝开了头,就会一个劲喝下去,直到连厨房里那座时钟也喝光。妈妈和我太熟悉这一切了,所以对所有能挑逗他酗酒的危险机会都怕得要命。葬礼,也是这种机会之一。
“我得上邓菲那儿去干半天活,”妈妈忧心忡忡地说,“可谁来照管拉里呢?”
“让我来吧,”爸爸和蔼地说,“走动一下对他也有好处。”
用不着多说,大家都明白,我才用不着别人照看,要让我留在家,我还能把索尼照料得好好的呢。要我跟父亲一道,是想让我充当他的制动器。尽管我这个制动器从来不灵,但妈妈还是认定我行。
第二天,我刚放学回来,爸爸已在家里。他替我和他煮了一盅茶。他煮茶是好手,但干别的手脚都太笨;他切面包的那个样子简直叫人打战。喝过茶,我们就走下斜坡上教堂去。爸爸穿着他最好的那套蓝哔叽,圆顶呢帽斜戴在头上,有点风流哥儿的味道。他在来送葬的人当中,发现了彼得·克劳利,真是高兴极了。彼得也是个危险信号,凭以往星期日早弥撒后的经验,我早就懂得这一点。就象妈说的,他是坏人,他参加葬礼只为了不花钱白喝酒。事实上他根本就不认识杜利先生!爸爸也有点瞧不起他,认为他还不如那些把血汗钱花在酒店里的笨蛋,因为他喝酒差不多从不自己掏腰包!
在爸爸看来,这葬礼够气派的。我们还没出发,还没冒着午后的阳光,跟在灵车后面朝墓地走去,他已经把一切都调查得一清二楚了。
“五辆马车!”他报道说,“五辆马车,十六辆蓬车!一位市府参事,两名地方议员,还有不计其数的教士。自从酒店老板威利·麦克死后,我还没见过谁的葬礼有这种排场。”
“这自然罗,他人缘好呀。”克劳利的沙哑嗓门响了。
“我的天,还用你来告诉我?”父亲尖声说,“难道他不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他去世前两天——仅仅两天哇——他那天晚上还到我家来着,把住宅合同的情况告诉我。市政府那些人全是强盗。不过,就连我也没料到他结交有这么广。”
爸爸快步朝前走,兴奋得象个小孩,周围的一切都叫他感兴趣:送葬者、山迪威尔路上的漂亮房屋。最危险的信号全出现了:阳光灿烂的天气,气派十足的葬礼,僧俗两方面的大人物。这一切都在挑逗、刺激,让父亲暴露出天性中虚荣、轻浮的一面。眼看他的老友被送进墓穴,他内心产生了一种类似欢愉的感觉,有种尽了义务的轻松感,而且也不无庆幸,不管以后在漫长的夏日黄昏,他会如何强烈怀念可怜的杜利先生,但毕竟是他想杜利,而不是杜利怀念他。
“咱们在人散前走吧。”爸爸悄悄对克劳利说,这时掘墓人才刚向穴里撒下第一锹土。父亲离开了墓地,蹦蹦跳跳的,活象头从一个草墩跳到另一个草墩的山羊。那些马车夫,虽然不象爸爸那样已经几个月没喝酒了,但瘾头似乎也不比他小,他们都满怀希望地抬头张望。
“那边快完事了吧,米克?”一位马车夫大声问道。
“快了,只剩下最后的祈祷啦!”听父亲说话那调门,活象在宣布什么特大喜讯。
离酒店还有几百码,马车队卷着尘龙超过了我们。虽然天气一热,爸爸腿就不灵便,但他还是加快了步子,还一面紧张地回头,看看大队的送葬者是否翻过岭来了。人群一到,你就可能要等啦。
我们到达酒店时,那些马车早已排成一行停在店外。系着黑领带、神气庄严的先生们正小心安慰那些神秘的女士,她们很庄重,只从放下的马车遮帘后伸出手来。酒店里只有马车夫和两个骚婆娘。我想,是刹车的时候了,于是就扯扯爸爸的衣角。
“爹,咱们现在就回家不好吗?”
“只等两分钟,”他满脸堆笑,十分亲切地说,“喝完一瓶柠檬水就走。”
这叫收买拉拢,我明白,但我一向是个意志薄弱的孩子。爸爸要了一瓶柠檬水和两品脱啤酒。我口很渴,一下就喝光了我的那份。爸爸可不象我,他几个月没喝过酒了,眼下可要慢慢地仔细地享受这无穷无尽的乐趣。他掏出烟斗,吹气通了通,装上烟丝,辟辟啪啪地划了几声火柴来点烟,他拼命吸着,眼珠都凸出来了。然后,他不慌不忙地转过身,背朝酒柜,一只胳膊肘支在柜台上,好象根本就不知道背后还有酒,慢条斯理地刷掉手掌上的烟末。他已安心要呆到天黑,从容不迫地逐一讲起他所参加过的盛大葬礼。马车全走了,那些次要的送葬者也拥进来了,店里已经半满。
“爹,”我又扯扯他的衣裳,“咱们回去吧。”
“呃,你妈还要过很久才能回家。”他说得还挺好听,“到外面马路上玩去,好不好?”
但我一听就知道是扯淡。一个人孤零零的,怎么能在陌生的街道玩儿呢?和以往一样,我很快就厌倦了。我知道爸爸挺能挨,非到天黑他是不会走的。我明白,恐怕我得领他回家了,他会醉得一塌糊涂,布拉尼巷的老女人们会全都跑到门口看笑话,说什么,“瞧,米克·德莱尼又醉啦。”我还知道,妈会着急得半疯,生怕爸爸第二天上不了工,这星期还没过完,她就得把那钟用披肩盖住,朝当铺里跑。厨房里要没个钟,静悄悄的,我怎么也习惯不了。
我的口还是渴。我发觉只要踮起脚尖,就够得着爸爸的酒杯。一个念头在我脑里一闪:试试杯里东西是啥滋味可是怪有趣的。爸爸背朝酒杯,是不会发现的。我拿下酒杯,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真扫兴。我真不明白他怎么能喝得下这种玩意。看来他是从来没沾过柠檬水的吧。
我本想劝他改喝柠檬水,可他正在一本正经地高谈阔论。他说,乐队是葬礼一个重要的附加成分。他摆出一副姿势,象倒持着一支步枪,哼了几节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克劳利敬佩得直点头。我又喝了一大口,马上就领略了黑啤酒的妙处。我觉得精神兴奋,心情开明而且达观。爸爸又哼了几节《扫罗》里的《死亡进行曲》。这酒店是个好地方,这葬礼也真够排场,我相信可怜的杜利先生在天之灵一定十分满意。同时我还想,他们可能也给他一个乐队。就象爸爸说的,乐队是重要的附加成分呀。
啤酒的妙处还在后头呢。它能叫你超脱自身躯壳,或者说使你飘飘然,就象腾云驾雾的六翼天使,在一旁观看你自己的模样。瞧你,两腿交叉,斜靠酒柜,超脱了琐事的烦扰,成人般思索深邃、严肃、有关生与死的问题。看着自己的模样,想想多滑稽,你一定会突然觉得很窘,总想咯咯笑出声来。可是,等我把一杯全喝完,这种状态也完结了;我发觉要把酒杯放回原处很困难,柜台象长高了不少。我的忧郁症又复发了。
“是啊,”爸爸一面向后伸手去拿酒杯,一面虔诚地说,“不论他在天堂还是地狱,愿上帝让这可怜人的灵魂安息!”他打住了,先瞧瞧杯子,又望望周围的人。“喂,”听他声音还挺和气,他还当是别人和他恶作剧呢,“谁干的好事?”
谁也没吭声,酒店掌柜和那两位老女人先看看爸爸,又望望他的酒杯。
“谁也没喝你的酒,我的好人。”一位女人忿忿不平地说,“你当我们是贼?”
“呃,米克,这儿是没人会干这种勾当的呀。”听口气掌柜也很惊讶。
“哼,是有人把我的酒偷了。”爸爸脸上的笑容消散了。
“真要有人喝,也只能是你身边的人干的。”那女人阴阳怪气地说,还狠狠地扫了我一眼。爸爸马上恍然大悟。我想当时我一定是醉眼乜斜的了。爸爸弯下腰,摇着我。
“你没事吧,拉里?”他大惊失色。
彼得·克劳利低头朝我呲牙直笑。
“怎么能叫人相信这种事?”
我能,而且毫无困难。我要呕吐了。爸爸生怕弄脏他那套好衣服,吓得往后一跳,连忙打开后门。
“快跑!快!快!”他喊道。
门口对面有堵攀满常青藤的墙,阳光正照在它上面。我拔腿就朝外冲。我的动机本来很好,可动作却过火了,因为我一扑,和墙壁撞了个正着,我心想,它该让我撞得够疼的了。我素来很讲礼貌,所以在和它碰第二次前,还说了声“对不起”。爸爸还是担心他那套衣服,他走到我背后,在我呕吐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扶住我。
“好孩子!”他鼓励道,“吐了就舒服了。”
天啊,我可不舒服,怎么也谈不上舒服。我一点也不顾他的面子,哇哇大哭起来,他领我回到店里,让我坐在那两位骚女人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她们愤慨地挺直身板,还在生父亲的气,怨他错怪了她们。
“老天爷啊!”一个女人呻吟般叫道,怜悯地望着我,“这德行,配做父亲么?”
“米克,”掌柜的慌张地说,他正朝我留下的污迹撤锯屑,“这里可不是孩子呆的地方。趁警察没发现,你最好赶快带他回家去吧。”
“仁慈的天父阿!”爸爸抽抽噎噎地说。他翻眼看天,无声地击掌,只有在六神无主的时候,他才有这副模样。“我倒了什么霉哟!他妈会怎么说啊?……女人就该呆在家里照管自己的孩子!”他咆哮着补上一句,显然是冲着那两个骚娘们说的,“马车全走了吗,比尔?”
“早走完了,米克。”酒店掌柜回答。
“那我领他回去吧。”爸爸垂头丧气地说,“我再也不带你出来了,”他恐吓我。“给,”他从胸袋掏出一根干净手帕,“按住你的眉棱。”
看见手帕上的血迹,我才知道自己的头破了。我的太阳穴马上砰砰直跳,我又嚎哭起来。
“嘘!别!别!”爸爸烦躁地说,领我出了店门,“人家还当你撞死了呢!这不要紧嘛,到家洗洗就好啦。”
“坚强些,老伙计!”走在我另一边的克劳利安慰道,“一会就没事啦。”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两个人,他们根本就不懂喝了酒会怎样。我一遇风,又被太阳一晒,酒力发作得更厉害了。我踉踉跄跄,摇摇晃晃,就象在风头浪尖上颠簸一样。爸爸又抽抽噎噎的了。
“全能的上帝啊!全街人都出来了!我怎么老是这么例霉!你就不能走好些吗?”
我走不好。但我看得一清二楚。布拉尼巷的娘儿们,不论老少,全让阳光引出来了。她们有的靠着矮门,有的坐在门槛上,现在全都停止饶舌,张开嘴巴观看眼前的怪事:两位毫无醉态的中年人,带着一个眉棱上开了道口子的、醉醺醺的小男孩回家。爸爸左右为难,一方面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快些让我藏进家里,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有必要解释一番,申明不是他的过错。后来,我们在罗奇太太的屋前停下了。街对面一家门前聚集着一群老太婆,我一看就讨厌,看样子她们对我全都太感兴趣了。我斜靠着罗奇太大家的墙壁,双手插在裤兜里,满怀伤感,怀念起可怜的杜利先生,他躺在克拉公墓冰冷的坑里,再也不能在这街道上迈步。我越想越动感情,就唱起了一首父亲最喜欢的歌。
墓穴冷冰冰,见不了明诺尼亚,也回不了钦科拉。
“唉,可怜的孩子!”罗奇太太叹道,“他的嗓子可不挺好的嘛,上帝保佑他吧!”
我也自认如此,爸爸却举起一根手指威胁我:“别嚷了!”这就叫我觉得真是咄咄怪事。也许是他还没意识到现在唱这支歌是正当其时吧,于是我就唱得更响了。
“住口,我叫你住口,”他尖声嚷道,接着又朝罗奇太太挤出一笑,“我们快到家了。让我抱你走吧。”
尽管我醉成了这样子,还不至于胡涂到这么丢脸,让人给抱回家。
“得了,”我声色俱厉,“你别打扰我好不好?我好好的,能走。只是我的头有点晕。只要歇一会就好的。”
“要歇就回家上床歇去。”他恶狠狠地说,想把我抱起来,看他满面通红,我知道他发火了。
“上帝呀,”我蛮横地说,“回家干什么?你他妈的就不能别管我?”
不知道为什么,对面街上那群老太婆觉得这很逗趣,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想到你喝上一滴酒左邻右舍就全都来笑你,我气得肚皮都快炸了。
“你们笑谁?”我吆喝,朝她们攥拳头,“再不让开我就打肿你们的脸,叫你们笑笑自个儿。”
她们却觉得更好笑了;我可从来没遇见过这么没教养的人。
“滚开,你们这帮脏母狗!”我咒骂。
“住口,住口!你给我住口!”爸爸收起强装出的好脸,咆哮了。他抓住我的手臂,抱着我就走。婆娘们的尖笑气得我发狂,爸爸的威胁气得我发疯。我拼命想站定不动,但力气小,哪里拗得过他,只好扭过头来朝那帮女人瞪眼睛。
“小心些,不然回头我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我叫骂道,“我要教训教训你们,叫你们懂得给体面人让路。你们该呆在家里,洗干净你们的脏脸。”
“马上全街人都传遍了,”爸爸抽抽噎噎地说,“不干了,再也不干了,哪怕能活一千岁我也不干了!”
直到今天我都还不清楚,当时他到底是发誓不再带我出门,还是说不再喝酒了。他把我拖进家里,为了显示我的英雄气慨,我嚷起了《韦克斯福德少年》这首歌。克劳利知道他留下会有麻烦,便溜了。爸爸替我脱了衣服,把我弄到床上,但我却睡不着,只觉得天旋地转,难受极了。我又吐了,爸爸弄了块湿布进来替我擦地板。我浑身发烫地躺着,只听见他劈柴生火,后来又摆弄餐桌。
突然,砰的一声,大门撞开了,妈抱着索尼一阵狂风似地冲了进来,她平素和蔼温顺的样子全没有了,换上了一副暴跳如雷的凶相。显然,邻居把什么都告诉她了。
“米克·德莱尼,”她歇斯底里地叫道,“你把我的儿子怎么啦?”
“嘘,女人,嘘!嘘!”爸爸连嘘了几声,左脚换右脚地蹦跳,“你想让全街人都听见?”
“哈,”妈发出吓人的怪笑,“街上的人早知道喽。谁还不知道?你和那头畜生为了寻开心,竟拿黄汤灌我倒霉的儿子。他好端端的犯了你们什么啦?”
“我可没给他酒呀!”他高声辩白,邻人对这倒霉事可怕的曲解叫他不胜惊骇,“趁我转过背去,他把酒喝了。天啊,妈的你把我都看成什么人啦?”
“哼,”妈尖刻地回答,“什么人,现在谁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上帝饶恕你吧,把咱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那几个血汗钱花去喝酒还不算,还想带坏儿子,让他也变成和你一样游手好闲的酒鬼。”
说罢她走进房里,在我床边跪下。看见我眉棱上的伤口,她不禁迸出呻吟。厨房里,索尼哇哇大哭了。一会儿,爸爸出现在房门口,他的帽子遮住眼睛,满脸自我怜悯的神情。
“好哇,我已经够倒霉的了,你还要这样责怪我,”他埋怨,“我一整天没沾过一滴酒。他都喝光了我还喝啥?要说可怜,该算我呢,白白花费一天,还要在满街人面前丢人现眼。”
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后就老老实实提着饭盒上工去了。他一走,妈妈就扑到我床边吻我。好象这全是我的功劳。她还要替我请假,等到我眼睛好些了才上学。
“我的小勇士!”她的眼睛发亮,“是上帝让你去的。你是他的守护天使。”
讨 论
在这个滑稽故事里,人物的位置颠倒了。成了家庭丑闻,引起邻居非议讥笑的事情不是父亲醉倒街头,年幼的儿子吓怕了,可怜巴巴地想把父亲领回家,不让他在众人面前丢丑。倒是小孩子醉步蹒跚,走腔走调大唱其歌,还咒骂女邻居是“脏母狗”,弄得父亲六神无主,心慌意乱。如果这故事只是简单地给我们讲述这颠倒离奇的情节,而且到此为止,那么,充 其量它也只能算一个博人一笑而已的笑话。它就不怎么象篇小说,甚至还算不上好笑话。因为隽永的笑话,也必须扎根于对人性的真正理解之中。
在这故事里,父子位置的颠倒不是一时之技。只要我们稍加追溯,就可以发现这种颠倒是贯串整个故事的。在对待父亲酗酒毛病的大事上,拉里这孩子接受了母亲的观点。他象个大人,关心家庭的利益,但同时还必须提防自己孩子气的弱点。拉里忧心忡忡,知道什么是坏“兆头”。他太熟悉父亲一开酒戒就会发生什么后果。他一直很关心父亲,直到啤酒对他起了作用,他的忧虑才头一次消失。
在故事里,倒是父亲有种孩童般的天真坦白,这种性格常常还很讨人喜欢。想想他参加葬礼时的高兴劲吧:“在爸爸看来这场葬礼够气派的。”他报道说有“五辆马车,十六辆篷车!”后来,拉里又说他,“眼看他的老友被送进墓穴,他内心产生了一种类似欢愉的感觉,有种尽了义务的轻松感,而且也不无庆幸,不管以后在漫长的夏日黄昏,他会如何强烈怀念可怜的杜利先生,但毕竟是他想杜利,而不是杜利怀念他。”后来,他告诉那些等着上酒店的马车夫,说下葬仪式快结束了:“‘快了,只剩下最后的祈祷啦!’听父亲说话那调门,活象在宣布什么特大喜讯。”而几分钟后,他进了酒店,准备开酒戒、解长渴的时候,更别提他有多高兴了!
如果拉里的父亲稍有些心计,或者稍为自觉,这种幽默的韵味就会失去,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对他就会采取另外一种态度了。他因为单纯天真闯了祸,也因为单纯天真获得读者谅解。与其说他有罪,还不如说他受罪——由于邻居婆娘们“可怕的曲解”,说他灌醉了自己的儿子,使他受到妻子责骂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显得突出。这位父亲的性格,不但与故事本质的意义有密切的关系,甚至还能决定我们认为这故事是不是真有趣的看法。尽管“一切情况都说明他不对”,他还是有种受到伤害的无辜的感觉。
人物位置大致颠倒的最逗笑的例子,就是在从酒店回家的路上,父亲并没有强迫叫叫嚷嚷、醉态蹒跚的儿子住口,而是哀求他清醒些,别嚷了——照常理推测,如果喝醉的是父亲,拉里也会这样对待父亲的。然而,这种颠倒逗笑的主要根源,却出自父亲的性格:如果他是个残酷野蛮的人,就会强迫儿子闭嘴。而这样父子就不会有什么逗人发笑的事了,一强迫,一粗暴,也放无幽默可言了。
这种颠倒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是在故事的末尾(也是故事的高潮),小孩子的淘气被曲解为神的安排,醉醺醺、摇摇晃晃在大街上出丑的小男孩,在母亲眼里却成了引导意志薄弱的父亲走正道的“守护天使”。我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笑——她赞扬拉里的说法,简直荒唐得象马拉柏洛柏太太①一样令人吃惊——不过,从她的观点来看,她的话也有相当道理:拉里成了小“男子汉”了。他使她少跑了一次常上的当铺。
1.拉里偷喝父亲啤酒这件事写得合情合理吗?拉里是否常干这类事?拉里父亲把酒搁在背后,让儿于喝光了都还不知道,这事可信吗?
2.作为一个孩子,拉里对他父亲的观察是否太成熟了?这故事是拉里事后不久就写的呢,还是隔了许多年,他成人后才写的?
3.这篇小说,情况的交待安排得很有技巧。请试加评论。迟迟不点出拉里父亲好酒,这样有什么好处?
4.拉里眉棱裂了个口子,这有什么重要意义?伤口和鲜血是否能为这意外事件增添某种反响?
5。是什么因素使得这故事不光是个笑话?如果你在答案中使用了“塑造人物”这术语,请解释你的意思。
①谢立丹的喜剧《竞争者》中的人物,以误用文字著名。
参考资料:blog.703804.com/?viewthread-451072.html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