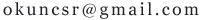苏式家具自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前期,前后四百余年,从形成、发展到逐步衰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特征。按照学术界的有些说法,由明入清至清代早期,是明式风格;清初以后是清式风格,并把交替时间确定在18世纪之初。笔者不认同这种区别,理由是苏式家具与京式家具、广式家具不同,自明以来作为明式家具的代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承继宋元家具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已形成一个独立体系。
雍正、乾隆时期,由于满清统治者的提倡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北方与南方分别产生了京式家具和广式家具,它们与苏式家具在新的历史时代的发展有许多差别,不能完全相提并论。即:无论是京式家具还是广式家具,并没有因为风靡一时而替代苏式家具,更没有使苏式家具改道换辙,也成了所谓的清式家具。相反,苏式家具在自己深厚的传统基础上,一方面仍生产着一定数量的保持“明式”传统的家具,另一方面,只是受到广式和京式的影响,在造型式样、装饰形式上出现了不少变体,表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征。但这类家具,并不像有人认为的已完全成了“清式”风格,与广式家具、京式家具完全一样,代表着新的时代精神。
清代的苏式家具不等同清式家具,正如明代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之外,全国都有家具生产,我们却不能认为这些家具全部是明式家具。因为,只有苏州地区以优质硬木为主要材料的细木家具,才被世人称之为“明式”,并视为中国古典家具中的杰出代表。至于其他区域生产的家具,有的风格不鲜明,缺乏特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有的尚处在开始形成阶段,未成规模。包括大量遍布全国的各种漆饰家具,精工细作的宫廷家具等,虽然与苏式家具的产生和形成同处一个历史时代,但由于“明式”的风格意义不具备,缺少鲜明的明式家具特有的文化特征,只能是另一风格范畴的典型。当然,也有些家具生产发达的地区,在明代苏式家具影响下,生产了一些相似的明式家具类型,但它们不是“苏做”,倒可以说是某些地区仿制了苏式家具或明式家具。只是到明末清初,苏式家具流行,各地相继也出现一些明式家具的生产,使中国古典家具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苏式家具与广式家具
地处我国南海之滨的广东地区,采用优质硬木为原料生产硬木家具的历史并不太晚,我们可以从一件面板底部刻有“崇祯庚辰(1640年)仲冬制于康署”的铁力木大翘头案为例证,说明迟至明朝末年就已有品质很好的高级家具了。这件由广东德庆县生产的翘头案,十分静穆气派,但与同时期成就显赫的苏式家具相比,仍略逊一筹。在造型比例、线脚运用和与形体的关系上都暴露出不足之处。这些年来,一直很少再有广东地区生产的明代高级硬木家具发现。1997年8月,笔者应邀赴广州作专题考察,顺道走访了《清代广式家具》的作者蔡易安先生。我们大致认定,广东地区明代优质硬木家具的生产要比苏州地区晚。广州地区开始较多的生产硬木家具可能是在清初,或许也是随着苏式家具影响的不断扩大而开始兴盛起来的。
到清代乾隆时期,广州地区的家具生产已非昔比,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正如《清代广式家具》中所分析的,“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清代广东家具领先突破了我国千百年来传统家具的原有格式,它大胆地吸取了西欧造型等新的家具形式,创造出了崭新的广式家具。”从风格上说,广式家具可以称得上是中西文化的合璧。今天,我们比照流传下来的广式家具,从造型形态、构造工艺、制作方法以及装饰纹样题材和表现形式,都能清楚地看到外来文化对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地巨大。它充分地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性,而这些,恰恰是同时代其他地区的家具所缺乏的因素。如苏式家具,始终没有如同广式家具一样的羊蹄脚、鲤鱼肚以及类似的部件装饰性符号或样式,包括运用西洋图案的雕刻手法。苏州地区虽然也有制造广式家具的产品,或者也流行一些广式家具的品种,这些产品和品种也只能是广式,是苏制的广式产品,而不能因为是苏州生产就称其为苏式家具。正像广州改制苏式品种的圈椅一样,总不免缺乏广式家具的形象和特色,也不能说其是广式家具,它实际上给人的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镶嵌大理石的盾形式靠背扶手椅、三连式和双连式长椅、通体雕刻的龙纹椅等等,才是广式家具无与伦比的代表产品;绞藤、连珠、仰俯莲瓣、西番莲花纹,双线花瓶脚、工字式连脚档、大挖弯以及满嵌螺钿、通体悬雕等等,才是广式家具最鲜明的风格特色。
这个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地域等各方面的原因,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家具制作显得因循守旧,传统的束缚使它们没有像广式家具那样在改革创新中冲锋陷阵。很快地,苏式家具在全国失去了它原先的主导地位,被广式家具取而代之,广式家具充当了时代的表率。
这时,沿着传统轨迹行进的苏式家具,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也进行着各方面的改良。被一些人捧为清式家具的开创者、革新者的李渔,其实就是苏式家具的一位改良者。这位出生于钱塘医家、富有天才的戏曲家和一代名流,长居金陵,到过苏州,游历了全国很多地方,还去过广州。他对物质功能的种种科学见解,在人与物之间提倡实用与精神统一的思想,同样体现在他对日常使用的家具设计中。他不仅自己设计暖椅、凉杌,主张箱、柜多置抽屉;还特别强调制器只有美材加良工才有真正的价值,并对“因其材美而取材以利用者未尽善”的现象提出了批评。然而,苏式家具的改良虽然使它失去了不少“明式”的精粹,跟着时代的推进发生了某些方面的变革,但依旧在传统的基础上走着自己的道路,依旧作为苏式而区别于代表“清式”的广式家具和京式家具,它是清代的苏式家具。
总之,明清之交,苏式家具把最负盛名的“明式”风格推上了历史的巅峰,同时,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保持了这一伟大传统,这是苏式家具最辉煌的岁月。清代中期后的苏式家具在改良中不断出现新面貌,并越采越受到广式和京式家具风格的影响,产生了各种变体,使苏式家具形成了许多新的形制和式样,但它没有像广式和京式家具一样,完全成为一种清式家具。
苏式家具与京式家具
大致与广式家具盛行的年代相当,由北京地区生产的清式家具,一般被称之为京式家具。北京是明清两代京城所在地,是最高封建统治阶层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在物质文化领域常常集全国之精华。宫廷内外使用的家具,从皇室到官宅,主要选用高级的漆饰家具,运用雕漆、镶嵌、描金、罩金、戗金、堆漆、填漆、彩绘、剔犀、犀皮等漆艺和装饰,使各类家具富丽堂皇,美不胜收。在苏州地区开始时兴优质硬木家具时,京城里对花梨木、紫檀木等细木工家具似乎并不热衷,故宫等遗存的家具实物资料中,明代的十分少见,有的也是因特殊需要而制作的。北京地区流传的明代苏式家具,可能主要是江南人入朝为官进京时从家乡带过去的,也有一些是通过其他各种途径,由商贩买卖而运送去的,但数量均不会太多。
清代早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我们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中不难知其大概。被认为绘于康熙朝晚期的这12幅屏风绢画,使我们看到了漆器家具和硬木家具在内府使用的真实情景。其中有不少漆饰家具,如榻、方桌、书架等,其款式和装饰与明代漆器一脉相承,而硬木制作的直背圆梗扶手椅和双圈结勾子头桥梁档桌子等,似乎就是江南地区生产的苏式家具,或者是宫廷仿制的苏式家具。这些采用优质硬木生产的苏式家具,对北京漆饰家具的生产不会不发生影响。
到了所谓的“清三代”盛世繁荣时期,硬木家具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于是很快地时兴起来,苏州、广州等地的能工巧匠更多地被招募到京城,专门设计制造硬木家具。但统治者的审美情趣与江南文人完全不同。一方面,皇宫大殿和内宫的环境需要隆重和气派,家具要有厚重的体量和架势,故常设计制作一些特殊功能的品种和式样;另一方面,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喜欢高贵、华丽和雕琢,使硬木家具显得五彩缤纷、富丽堂皇。加之充足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一味崇尚精细繁华、光怪陆离的效果,使宫廷家具无论是重材质,施巧工,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清代硬木家具的艺术风格,在这一地区又产生了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和面貌,显示出别开生面的气象。其中不乏雍容大度、精丽高雅、美轮美奂的优秀作品,它们同样作为清式家具的代表而与广式家具并驾齐驱。从某种意义上说,京式家具比广式家具更富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它使清式家具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水平在某些范畴中得到了提高。
显而易见,北京地区的硬木家具,更多地吸收了漆饰家具的传统和特色,南方地区则受到西方文化的侵入,从而各自产生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这些风格特点又反过来影响苏式家具,特别是乾隆以后,使苏式家具表现出了许多“清式”因素,产生了所谓传统优质硬木家具的“变体”形态。首先,它突出地加强了家具形体自身框架构成的结构变化,从四平八稳的传统程式化的架式中,努力创造出许多新颖的形制和式样来,使苏式家具的造型出现了新的面貌和新的款式。例如扶手椅中的直背椅、云钩扶手椅,案桌中的各种小型书桌、五花八门的琴桌以及圆形类的家具等等,都大大地突破了明式的一贯形式,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受和丰富的审美情趣。这种结构的变化还更进一步促进了传统细木工艺水平的提高。其次,在装饰上,不仅摆脱了墨守成规的装饰手法,且运用多样的装饰材料,加强了家具的视觉艺术效果,增强了造型的形象感染力。但是,苏式家具在时代变化中,仍一如既往地固守几百年来的传统。尽管推动之下的变革也时有所显,但只是局部的,有限的,这就是与广式和京式不相吻合、不能同一的原因。
总而言之,在江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社会结构、经济生活和文化艺术土壤中孕育产生的苏式家具,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以其独特的时代风格和艺术特征在明清家具中最负盛名,并由此而成为中国古代传统家具的经典。同时,清代早中期以后京式和广式家具也在新的历史发展中创立起新的时代式样,形成了新的风格和特色,从此也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和价值。
参考资料:摘自《收藏家》2002.07 作者:濮安国
什么是清式家具的“三式”?
清代的苏式家具不等同清式家具,正如明代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之外,全国都有家具生产,我们却不能认为这些家具全部是明式家具。因为,只有苏州地区以优质硬木为主要材料的细木家具,才被世人称之为“明式”,并视为中国古典家具中的杰出代表。至于其他区域生产的家具,有的风格不鲜明,缺乏特定的文化内涵...
清式家具有什么特点?我想仔细了解一下,哪个资深人士解答下?
清式家具 用材厚重,形体宽大,装饰奢华,体现厚重,豪华,富丽堂皇的风格。清式家具分为三大名作,广式 苏式 京式。广式最为统治阶级欣赏,广式家具的特点是1:用料粗大充裕2:木质一致3:花纹雕刻深峻,刀法圆熟,磨工精细4:装饰题材和纹样收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或多或少具有西洋风格。苏式...
古代清式家具:椅类
清式家具,起源于清康熙年间,盛行于乾隆时期,以其独特的工艺美术风格著称。清代早期家具继承明代风格,乾隆年间则吸收了多种工艺美术手法,形成了清式家具风格。清式家具选用紫檀、红木、酸枝、柚木等优质木材,色彩以深色为主,故宫传世珍品多为此类材质。清式家具品种繁多,制作工艺精湛,造型和装饰成为...
清代家具的发展阶段
我们一般说的清代家具指的就是清代中期的家具,即指康熙未至雍正、乾隆、以至嘉庆初的清代中期这一段清盛世时期的家具。这段盛世家具风格的形成,的确与清代统治者所创造的世风有关。表现了从游牧民族,到一统天下的雄伟气魄,代表了追求华丽和富贵的世俗作风。由于过份追求豪华,而带来一些弊端,也是存在的。但是,清式家具...
清式家具的特点是什么
清式家具简介清式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工艺在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因社会文化上出现了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繁缛雕琢的奢靡颓废风气以及“广式家具”的盛行和满清宫内院对奢靡挥霍风气的跟风追随和提倡,从而形成的大多以造型厚重、形体庞大、装饰繁琐的家具风格,在形式和格调上与传统家具的朴素大方、典雅...
解析明清家具
明式家具,是指明代家具式样的家具,它可以是明代生产的,也可以是清代生产的。仿明家具,则指现代仿造明代的家具。 为 什么要搞清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国古代家具是个完整的连续过程,我们所说的宋代家具、明代家具或清代家具,一般是指这一时期的家具,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工艺的发展不可能像必朝换代那样容易...
清代家具的种类?
1、床、宝座。主要有架子床、罗汉床和宝座,比较明式的多,其风格与明式大不一样。2、椅、凳、墩。种类与明式大体相似,造型及装饰风格却不同。3、桌、案、几等承具。4、屏风。清代屏风种类齐全,主要有插屏、挂屏、围屏、座屏等,从而更能体现清式家具的风采。5、柜、格、箱、架。风格与明式大...
清代家具风格特点的三个阶段
这时的家具生产不仅数量多,而且形成为特殊的、有别于前代的特点,或叫它风格。这风格特点,就是 清式家具 风格。1、造型上浑厚、庄重 这时期的家具一改前代的挺秀,而为浑厚和庄重。突出为用料宽绰,尺寸加大,体态丰硕。清代大师椅的造型,最能体现清式风格特点。它座面加大,后背饱满,腿子粗壮...
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的区别
硬木家具 的部件和零部件,如抽屉板、桌底板及穿带等,所用的木料都是硬木。 清式家具的样式也比明朝繁多,如清朝新兴的家具太师椅,就有三屏风式靠背太师椅、拐子背式太师椅、花饰扶手靠背太师椅等多种。2、用材广泛,装饰丰富。清式家具喜于装饰,颇为华丽,充分应用了雕、嵌、描、堆等工艺手段。
清式家具特点
第一,清式家具在选材上,一般都会偏爱木质家具,并且主要是喜爱选用质地较好纹理清晰的硬质木料,典型的清代家具木料主要是以紫檀为主。并且在紫檀木的选用上也是非常考究的,都是上等紫檀木才会被选用。第二,在制作上,为了保持木料的原始质感与气息,清代家具大多都是一木连坐,而不是多款木料拼接。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