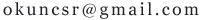屈原(约前340—约前278)是我国最早一位爱国诗人,战国时楚国人,出身贵族,学识渊博,明于治国之理,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他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却遭谗去职,被放逐江南,多年流浪辗转于沅湘流域。当他看到强大的楚国日渐衰落,忧心国事,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九章》、《九歌》、《招魂》、《天问》、《离骚》等。他在名篇《橘颂》中用拟人手法将橘树理想化和人格化。“受命不迁”、“深固难徙”,喻意自己执守的品格、道德、节操,也隐示了诗人50年后投水自沉的绝决之念。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楚国君臣仓皇出逃,百姓惨遭涂炭。理想的毁灭,国家的危亡,人民的苦难。使屈原痛不欲生。是年旧历五月初五,他自投汨罗江而死。后世人民为表达对屈原崇敬怀念的心情,就在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吃粽子、赛龙舟。
楚文化有崇“九”传统。屈原作品就有《九歌》、《九章》,他的学生宋玉也有《九辩》。《楚辞》中许多地方用到“九”字、如九天、九畹、九州、九疑、九坑、九河、九重、九子、九则、九首、九衢、九合、九折、九年、九逝、九关、九千、九侯等,可见“九”在楚地信仰中影响之大。有人认为《九歌》的“九”字泛指多数,有人认为“九”可读为“鬼”,至今尚无定论。《九歌》并不限于9篇,而是有11篇。其中:《东皇太一》祭祀天神;《东君》祭祀太阳神;《云中君》祭祀女性云神;《湘君》祭祀湘水男神;《湘夫人》祭祀湘水女神;《大司命》祭祀寿命之神;《少司命》祭祀子嗣之神;《河伯》祭祀河神;《山鬼》祭祀女性山神;《国殇》祭祀阵亡烈士;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之曲,为各篇所通用。这些篇章可以由男女巫觋来表演,以表现人神交会等场面。
楚国兴起于江汉流域,殷商时已与北方政权发生联系,春秋时得到迅速发展,已足经和中原抗衡。楚国地域广大,川泽山林遍布,物产十分富饶,地理环境优越,在长期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与中原地区的“礼乐文化”不同,地处偏远的楚文化吸收了土著民族巫鬼信仰和歌舞祭仪的某些特征。而楚国国君对这种巫鬼祭祀之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乐歌的起源与巫术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歌舞都是全民性的歌舞,后来才渐渐分化出善歌善舞的专门人才,女性称“巫”,男性称“觋”。巫觋主祭司舞,装神弄鬼,先民相信他们可以上达人的祈愿、下传神之旨意。在氏族部落和奴隶社会的神权、族权统治下,巫觋享有特殊地位,他们又是人类中最早的歌舞艺术家和教师。原始乐歌中祀神的乐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内容可以概括为神歌、情歌两大体系。情歌在原始时期同祀神乐歌融为一体“以乐诸神”,后随文明的演进才逐渐分化出来。三峡地区原始乐歌的最大特色是“巫音”、“巫风”,在现代流传的传统民歌中仍然能见到“巫音”的痕迹。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被放逐到楚国南部的沅水、湘水一带,他发现这里巫风兴盛,人们信鬼神、重祭祀,“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故而“更定其词”,对这些比较粗陋的民间祀神歌舞进行了加工,创作了一组优美的祭祀用歌舞套曲——《九歌》。久远的年代,使巫觋活动掩埋于尘埃之中。所幸的是,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屈原的《九歌》里,感受到祭神礼仪的盛况。
《九歌》在形式上延续了“巫觋文化”的形式,但其内容已不再是单纯的祭祀鬼神,而是蕴含了屈原的主观情感,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艺术创作,在形式上超越了自我身世感怀和个人际遇,因而也就更单纯、更自由、更健康、更富于想象力;由于《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所以它也就更加具有楚国的地域气息和神秘色彩。具体说来,《九歌》中的任何一段都具有独特的切入角度和意象体验,将我们带到一种飘渺恍惚的仙境。“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中关于祈神降临的这段描写,用秋兰点缀优雅环境,体现了祈神者的圣洁与虔诚,满堂的“美人”都在期待着那激动人心的场景。然而,无影无形的神灵却情有独钟地依附在巫师的身上,其精神的沟通就像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美好的时刻稍纵即逝,当来去无踪的少司命御风归去之时,巫师不由地发出了生离死别的慨叹。然而,这既是永远的别离,又是永恒的怀念。在这里,屈原将神秘无比的降神仪式描绘成男女之间的情感缠绵,在大胆的笔法和丰富的想象之中,加入了俗世的体验和人性的温情。读来感人至深。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中的这一段描写也很精彩。“山鬼”本应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怪物,作者似乎为了克服人们的恐惧心理,第一句便把它描绘成一个人的形象,从而在感情上拉近了它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然而“若有人”还不就是人,倘若山鬼完全长成人的模样,那又何其成为“山鬼”呢?因此这个人形之鬼还必须“被薜荔兮带女萝”。即用山上常见的藤蔓植物以妆点其“山”的形象、“鬼”的特征。于是,已被拉近的距离又被故意推远了。第三句最为巧妙,它不仅以“含睇”和“宜笑”两个词将远处的描摹变为局部的特写,而且再次以情感的方式缩短了读者与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在这种眉目传情、秋波流转的姿容里,我们所看到的已不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怪物,而是一位风情万种的女子了。
从表演形式上看,《九歌》很像一出化装歌舞剧,分角色歌唱,乐队丰富,有钟、鼓、琴、瑟等乐器,采用了独唱、对唱、领唱、合唱等形式,有独舞,有群舞,且有简单的情节。比如《湘君》和《湘夫人》就可以看做是一出戏的上本和下本。《湘君》写湘夫人到达约会地点,没有见到湘君而对湘君产生的思念;《湘夫人》则写湘君前来和湘夫人约会,没有见到湘夫人而对湘夫人泛起的怀恋。男巫和女巫分别扮演湘君和湘夫人,在歌舞演唱中充分展现这对配偶神相约、企盼、失望、哀怨等情怀。因此,有学者认为,这里已经具有了戏剧艺术的雏形。
大傩图屈原的《九歌》中充盈着放纵恣肆的想象与浪漫的情怀,由此推想,远古巫术仪式中的《九歌》及夏启操演的《九歌》想必也与此相类似。巫文化的流风遗俗自汉以后在中华文化中已难觅踪迹,但从《九歌》中,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到那迥异于中原乐舞的狂放激情。
《九歌》中多数篇章都是描写神灵间或人神间的恋情,凄艳幽渺,流露出深切的思念和所求未遂的哀伤,洋溢着人世间的生活气息。而屈原的另一部作品《九章》主旨则接近于《离骚》,主要反映诗人两次被放逐的经历和苦闷的心情,表现诗人爱国热情和对昏君群小的无比痛恨,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浓厚的抒情成分完美结合。其中《涉江》具体描写了诗人在流放中的痛苦生活,同时也表达了诗人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他向世人郑重宣告:“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天问》是对天地万物的质问,体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对事物进行探究的精神。《招魂》极写世间的险恶和故乡的美丽,表达诗人忠贞不渝的爱国热忱。总之,屈原以一己之身开创的文学传统,使楚文化以致整个长江流域文化能够与黄河文化比肩,从此,中国文学舞台上风骚双璧,交相辉映。前人有“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语一个危亡的国家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是国家的不幸,却是文学史上的大幸。而以国家为代价换取来的荣誉,当然不是屈原所希望得到的,他的最终理想还是国泰民安、天卞太平、壮志能酬。
因此,屈原用宏伟博大、奇情壮彩的诗篇树立起我国第一个浪漫主义高峰。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将《九歌》誉为“金相玉质、百世无匹”的作品。而他的爱国热情、高洁哀婉的个性、执著不屈的悲剧品格、怨刺愤激的精神气质、绚丽浪漫的艺术手法,都对后世的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贾谊曾著《吊屈原赋》寄予他对诗人的敬仰和怀念,以及对自己壮志难酬的感慨。司马迁感同身受,在《史记》中专为屈原立传,悲呼屈子“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一身傲骨的李白也赞“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所有的这些评价和赞扬都表达了文人诗客对屈原深深的敬意。江淹、杜甫、李贺、陆游等诗人也都写下了颂扬屈原的诗篇。最清绝的是张孝祥的《水调歌头·泛湘江》:“濯足夜滩急,唏发北风凉。吴山楚泽行遍,只欠到潇湘。买得扁舟归去,此事天公付我,六月下沧浪。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制荷衣,纫兰佩,把琼芳。湘妃起舞一笑,抚瑟奏清商。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莫遣儿辈觉,此乐未渠央。”显然,屈原的个体感受已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共同情感体验。因此,《九歌》才深深震撼了后人的心灵,感天动地,千古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