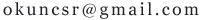来源:
家族作为文化载体,它是随时代而发展的,亲历了人类经验中一切兴衰变迁,是认识人类进程的珍贵标本.因此,家族小说历来是中外文学表现复杂的历史和人文世界极灵活而丰富的叙事.在转型期相对复杂的文化语境下,作家们对以家族/血缘视角切入历史叙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些文本不仅从宏大历史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而且也改变了中国传统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在将家族作为一种故事枢纽和文化载体的同时,又将它深植到人类精神的痛苦性本源上,并以此作为审视的契口,辐射出作者对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当代史的全面思考.从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逃脱历史阴影的果断、决绝与文化重建的艰辛、苦痛.故而,激进热烈与悲壮苍凉,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小说与世纪之交小说进行家族历史叙事之时的美学风格差异,这实际上也显现出中国当代作家在民族现代化历程中的一条心灵轨迹.
家”是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题材,自五四以来,关于“家”的叙事层出不穷,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之后,又掀起了一股“家族”题材热,陆续又出现了张炜的《古船》、《家族》,苏童的“飞越枫杨树系列”,李佩甫的《李氏家族》,陈忠实的《白鹿原》,王旭烽的《南方有嘉木》,阿来的《尘埃落定》,李锐的《旧址》、《银城故事》,莫言的《丰乳肥臀》,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毕飞宇的《叙事》,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家族小说。这两种叙述体现了“出走”和“回归”的完全不同的流向。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作为“伤痕文学”重要起源的卢新华的《伤痕》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伤痕》也成为二十世纪从“出走”到“回归”的一个重要转折。小说的前半部分讲述的是一个“出走”的故事:主人公王晓华是一个“林道静”式的人物,为了保持革命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而和家庭决裂,与“戴瑜式的人物”———母亲,划清界限。小说的后半部分则是一个“回家”的故事,在母亲的信中,两次提到:“孩子,早日回来吧。”虽然,最后王晓华回来之时,已人去楼空,母亲病逝,但故事的结尾,王晓华仍然找到了昔日的男友,往日的情感,找到了“回家”的路。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从现代革命伦理向传统血缘和家庭伦理回归的症候。然而,正如人们通常对“伤痕文学”的评价那样:“伤痕文学”重在揭露、思考“文革”给人所造成的政治上的伤害,是一种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所以,《伤痕》的“回家”并不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归来。
一九八六年发表的莫言的《红高粱》是当代家族小说的开辟之作。《红高粱》宣言要“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将历史叙述从“国家”和“革命”的控制之中拯救出来。在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写道,“我曾经到过长江下游的旧日竹器城,沿着颓败的老城城墙寻访陈记竹器店的遗址”,寻找“我的家族从前的辉煌岁月”。他们借助“寻根文学”的潮流和南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爆炸”的氛围,寻找到和确立了自己新的书写方向。与《林海雪原》和《红旗谱》革命文化对“民间”的征服和“家族”的收编不同的是,《红高粱》重新释放了“民间”复杂的内涵:“我应该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旗帜,把那里的土地、气候、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怨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1]因此,黄子平说,《红高粱》代表了“‘英雄好汉王八蛋’最终重新‘反出江湖’的文学史历程”[2]。《红高粱》成为了“寻根文学”和“家族小说”的交汇点。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整个家族传奇的背景是一个原始野性的荒野,而不是传统规范和道德化的“家”。“我爷爷”和“我奶奶”身上充满了叛逆的因子,“我爷爷”“杀人越货”,“我奶奶”“不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3]。“我奶奶是个性解放的先驱”由两套不同的语言符号组成,“我奶奶”代表家族血缘、宗法文化,“个性解放”则是现代语言和西化观念。在《红高粱》中,国家话语和家族话语、大叙事和小叙事、国家正史和民间野史两股叙事语流相互纠缠交织,难分难解。所以,这里作者的态度是含混的,既有“寻根”——对家族史、家族血脉的追寻,也有“反叛”——现代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反叛精神和作为“未完成的启蒙”的“现代”。可以说,诞生于一九八○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里的《红高粱》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回家”。
真正的“回家”有待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家族小说《白鹿原》和《旧址》的出现。如果拿《白鹿原》和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家》进行对比的话,那么,《白鹿原》中的“黑娃”其实就是《家》中的“觉慧”,而“田小娥”也就是五四时期的“娜拉”。在《白鹿原》中,作者赋予了反叛人物以完全不同的命运,黑娃最后“认祖归宗”,跪倒在祠堂面前,而田小娥最后骨灰被烧三天三夜,并压于“六棱砖塔”之下。被归并到“新历史小说”之中的一九九○年代的家族小说通过对于二十世纪革命的反思和否定以及对家族伦理和传统儒家文化的重新认同,在某种意义上汇入了九十年代“告别革命”的“日常生活”潮流。
在李锐的《银城故事》中,二十世纪反复书写的革命与家族之间的冲突转向了新的情节和诠释:“如果自己也像欧阳朗云一样没有家室的拖累,没有家族的后顾之忧,在面临杀身之祸的时候,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牵挂和煎熬了。”[4]在《旧址》中,银城历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革命的女英雄——李紫痕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家族守护者,“革命”的理由和原因竟然不是“阶级感情”而是家族的手足之情:“李乃之没有想到,自己经过七年读书思考才做出的抉择,姐姐竟在一夜之间就做出了。第二天早晨,姐弟俩人在饭桌前坐下来的时候,李紫痕毅然决然地告诉弟弟:‘弟弟,我也革命。要死我们骨肉死在一起!’”[5]李锐的这两部小说否定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原理和逻辑,而把家族亲情与伦理重新植入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的动力之中。欧阳朗云的招供使得为“革命”而“离家”也变得毫无意义。与《红旗谱》这种现代家族叙事将家族复仇转变为阶级斗争和融入到一种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不同的是,在周大新的《第二十幕》中,贯穿尚家家族的是家业振兴的精神,正如小说中卓远为女儿容容分析得那样:“这种家庭通过辈辈相传的教育,让为实现那个目标而奋斗的精神深深浸入他们家庭成员的血液和头脑,使实现那个固定目标成了这个家庭成员活在世上的目的。”[6]不是阶级和民族国家,而是家族重新成为叙事和历史的目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家族小说的兴起无疑和中国思想界与知识界“告别革命”以及重返“日常生活”的思想史脉络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正如新文化运动启蒙导致了现代文学的“出走”,“告别革命”则导致了“新时期文学”最终对于家族的重新认同和家族的回归。
所谓“出走”是和“个人解放”、“婚姻自由”等启蒙主义话语联系在一起的。最初将“出走”这一概念付诸于实践的并非经济或政治原因,多数是婚姻自主的问题,特别是女青年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恋爱自由而抗婚出走。中国的娜拉——鲁迅《伤逝》中的主人公子君“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宣言和她的出走构成了二十世纪最耀眼、最壮丽辉煌的一幕。“出走”成为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最具光彩、最引人注目的姿态,在中国现代历史开幕这一刻所塑造的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态具有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亮相”一样的意义。二十世纪初,摧毁贞节等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教,生成了中国妇女解放汹涌澎湃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中,放足、剪发、男女同校、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同居,使妇女解放运动首先直接地体现为“身体”的“解放”。五四的“女儿们”把自己从家庭和家族中解放出来并不是自律自为的运动,而是服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目的,依附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妇女解放最初是由于国家的召唤,也就是说,“国家”把她们作为“国民”从“家庭”和“家族”的控制和男性的占有中解放出来,并直接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妇女走出家庭,获得曾经为男性所垄断的人的基本权利往往都是由于国家、尤其是民族战争的需要。正如伍尔夫所说的:“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7]现代妇女解放的历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她们在“国家”的怂恿和支持下砸碎“家庭”枷锁融入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过程。
左右相连的平行性叙事,以悌为主题。
所谓“现代化叙事”最初产生于西方,八十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其主题是论证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经济增长因素、制度创新与政治参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等成为观察,认识现代化问题的框架。
“现代化叙事”是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置放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下来认识,而这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是在深受外国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叙事”也把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置放于社会变迁的大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化动力、范围、速度、现代化的主体与客体等的研究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层面相。这种从八十年代引入的叙事方式对现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之后,又掀起了一股“家族”题材热,陆续又出现了张炜的《古船》、《家族》,苏童的“飞越枫杨树系列”,李佩甫的《李氏家族》,陈忠实的《白鹿原》,王旭烽的《南方有嘉木》,阿来的《尘埃落定》,李锐的《旧址》、《银城故事》,莫言的《丰乳肥臀》,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毕飞宇的《叙事》,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家族小说。这两种叙述体现了“出走”和“回归”的完全不同的流向。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作为“伤痕文学”重要起源的卢新华的《伤痕》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伤痕》也成为二十世纪从“出走”到“回归”的一个重要转折。小说的前半部分讲述的是一个“出走”的故事:主人公王晓华是一个“林道静”式的人物,为了保持革命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而和家庭决裂,与“戴瑜式的人物”———母亲,划清界限。小说的后半部分则是一个“回家”的故事,在母亲的信中,两次提到:“孩子,早日回来吧。”虽然,最后王晓华回来之时,已人去楼空,母亲病逝,但故事的结尾,王晓华仍然找到了昔日的男友,往日的情感,找到了“回家”的路。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从现代革命伦理向传统血缘和家庭伦理回归的症候。然而,正如人们通常对“伤痕文学”的评价那样:“伤痕文学”重在揭露、思考“文革”给人所造成的政治上的伤害,是一种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所以,《伤痕》的“回家”并不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归来。
一九八六年发表的莫言的《红高粱》是当代家族小说的开辟之作。《红高粱》宣言要“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将历史叙述从“国家”和“革命”的控制之中拯救出来。在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写道,“我曾经到过长江下游的旧日竹器城,沿着颓败的老城城墙寻访陈记竹器店的遗址”,寻找“我的家族从前的辉煌岁月”。他们借助“寻根文学”的潮流和南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爆炸”的氛围,寻找到和确立了自己新的书写方向。与《林海雪原》和《红旗谱》革命文化对“民间”的征服和“家族”的收编不同的是,《红高粱》重新释放了“民间”复杂的内涵:“我应该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旗帜,把那里的土地、气候、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怨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1]因此,黄子平说,《红高粱》代表了“‘英雄好汉王八蛋’最终重新‘反出江湖’的文学史历程”[2]。《红高粱》成为了“寻根文学”和“家族小说”的交汇点。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整个家族传奇的背景是一个原始野性的荒野,而不是传统规范和道德化的“家”。“我爷爷”和“我奶奶”身上充满了叛逆的因子,“我爷爷”“杀人越货”,“我奶奶”“不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3]。“我奶奶是个性解放的先驱”由两套不同的语言符号组成,“我奶奶”代表家族血缘、宗法文化,“个性解放”则是现代语言和西化观念。在《红高粱》中,国家话语和家族话语、大叙事和小叙事、国家正史和民间野史两股叙事语流相互纠缠交织,难分难解。所以,这里作者的态度是含混的,既有“寻根”——对家族史、家族血脉的追寻,也有“反叛”——现代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反叛精神和作为“未完成的启蒙”的“现代”。可以说,诞生于一九八○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里的《红高粱》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回家”。
真正的“回家”有待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家族小说《白鹿原》和《旧址》的出现。如果拿《白鹿原》和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家》进行对比的话,那么,《白鹿原》中的“黑娃”其实就是《家》中的“觉慧”,而“田小娥”也就是五四时期的“娜拉”。在《白鹿原》中,作者赋予了反叛人物以完全不同的命运,黑娃最后“认祖归宗”,跪倒在祠堂面前,而田小娥最后骨灰被烧三天三夜,并压于“六棱砖塔”之下。被归并到“新历史小说”之中的一九九○年代的家族小说通过对于二十世纪革命的反思和否定以及对家族伦理和传统儒家文化的重新认同,在某种意义上汇入了九十年代“告别革命”的“日常生活”潮流。
在李锐的《银城故事》中,二十世纪反复书写的革命与家族之间的冲突转向了新的情节和诠释:“如果自己也像欧阳朗云一样没有家室的拖累,没有家族的后顾之忧,在面临杀身之祸的时候,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牵挂和煎熬了。”[4]在《旧址》中,银城历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革命的女英雄——李紫痕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家族守护者,“革命”的理由和原因竟然不是“阶级感情”而是家族的手足之情:“李乃之没有想到,自己经过七年读书思考才做出的抉择,姐姐竟在一夜之间就做出了。第二天早晨,姐弟俩人在饭桌前坐下来的时候,李紫痕毅然决然地告诉弟弟:‘弟弟,我也革命。要死我们骨肉死在一起!’”[5]李锐的这两部小说否定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原理和逻辑,而把家族亲情与伦理重新植入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的动力之中。欧阳朗云的招供使得为“革命”而“离家”也变得毫无意义。与《红旗谱》这种现代家族叙事将家族复仇转变为阶级斗争和融入到一种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不同的是,在周大新的《第二十幕》中,贯穿尚家家族的是家业振兴的精神,正如小说中卓远为女儿容容分析得那样:“这种家庭通过辈辈相传的教育,让为实现那个目标而奋斗的精神深深浸入他们家庭成员的血液和头脑,使实现那个固定目标成了这个家庭成员活在世上的目的。”[6]不是阶级和民族国家,而是家族重新成为叙事和历史的目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家族小说的兴起无疑和中国思想界与知识界“告别革命”以及重返“日常生活”的思想史脉络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正如新文化运动启蒙导致了现代文学的“出走”,“告别革命”则导致了“新时期文学”最终对于家族的重新认同和家族的回归。
所谓“出走”是和“个人解放”、“婚姻自由”等启蒙主义话语联系在一起的。最初将“出走”这一概念付诸于实践的并非经济或政治原因,多数是婚姻自主的问题,特别是女青年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恋爱自由而抗婚出走。中国的娜拉——鲁迅《伤逝》中的主人公子君“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宣言和她的出走构成了二十世纪最耀眼、最壮丽辉煌的一幕。“出走”成为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最具光彩、最引人注目的姿态,在中国现代历史开幕这一刻所塑造的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态具有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亮相”一样的意义。二十世纪初,摧毁贞节等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教,生成了中国妇女解放汹涌澎湃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中,放足、剪发、男女同校、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同居,使妇女解放运动首先直接地体现为“身体”的“解放”。五四的“女儿们”把自己从家庭和家族中解放出来并不是自律自为的运动,而是服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目的,依附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妇女解放最初是由于国家的召唤,也就是说,“国家”把她们作为“国民”从“家庭”和“家族”的控制和男性的占有中解放出来,并直接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妇女走出家庭,获得曾经为男性所垄断的人的基本权利往往都是由于国家、尤其是民族战争的需要。正如伍尔夫所说的:“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7]现代妇女解放的历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她们在“国家”的怂恿和支持下砸碎“家庭”枷锁融入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过程。
“娜拉”的“出走”实际上是没有出路的,鲁迅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并进而提出了“争经济权”的问题。伍尔夫说:“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8]因此,历史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开始转向了一九二○年代激烈的政治和经济“革命”——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无论是“娜拉”的出走,还是政治的“革命”,在根本上都是因为二十世纪严重地提到了中国人面前的民族国家的课题,二十世纪的一系列叙事都离不开“破家立国”这个故事。“个人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故事不过是民族解放的大故事里的一个小故事。“新民”不过是“新中国”规划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和插曲。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指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9]所谓“革命”,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的革命。为了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必须摧毁国家与个人之间重要的障碍———家族。
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开端,对“家”的批判和否定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一方面是“家”的毁灭,另一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中国,“个人”的身体及其心灵构成了“家”/“国”之间争夺的一个最重要的场所。二十世纪,在民族主义话语支配下,“家”丧失了对于个人控制的合法权力,与此同时,个人则被供奉到“国家”的神圣祭坛上。而“家族制度的罪恶”根本在于阻碍了现代民族主义的目标。一九一九年一月,在《新潮》创刊号上发表的傅斯年的《万恶之原》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读者诸君! 请猜我说这万恶之原,是甚么东西呀! 我想大家永不会猜到。”几个月来“读书、观察、思考的结果”,万恶之原是中国的家庭[10]。一九一四年,吴贯因在《改良家族制度论》中说:“中国之社会,有一根深蒂固之制度,足以阻碍国家之进步者,则家族制度是也。国家之发达,必其全国人民,其精神与国家接近,人民之心思材力,于自营一身之外,其余力不复他用,而悉举以贯注于国家,夫而后其国能蒸蒸焉日进于上。若夫国家与人民之间有一阶级焉,阻其直接之关系,使人民之心思材力,其作用为此阶级所圈限,而无复余力以顾及国家,则其国家终无由发达,故欲导其国之政治,使日进于文明,则此贯注于国家与人民间之家族制度,虽前此曾收其利,而以有碍于国家之进步,实当宁从割爱,而勿使为政治上之阻力也。”[11]他后来在《改良家族制度后论》中更明确申论:“抑吾对于家族问题,所以言之不厌其详者,诚以中国现在之家族制度,非改良更张,则举国之人,其精神财力,将为其销耗以尽,更安能有所贡献于国家。而以今日兢尚军国主义时代,独欲以宗法主义立国,其国未有不亡者,故此事能否改良,实国家存亡之所系也。”[12]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写道:“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来没有一次具有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13]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构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国对“家”和“家族”的激进的经济和政治革命发生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时也伴随着对于“家”的文化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样板戏中,传统的“家”被摧毁了,代之而起的是超越了传统“血缘伦理”的“革命伦理”和“革命家庭”,而最典型的莫过于《红灯记》中的新型的“革命家族”:“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我姓李,你姓陈,你爹他姓张。”革命摧毁了传统的伦理和家族,同时建立了新的现代革命伦理和认同:“都说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因此,“文化大革命”体现了毛泽东对于一种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想。毛泽东是以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达到梁启超提出的“新中国建设”——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从晚清的“富国强兵”到一九六四年提出“四个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根本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它以一种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方式来构建和造成一个“新中国”。
简述八十年代家族叙事有哪两大分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之后,又掀起了一股“家族”题材热,陆续又出现了张炜的《古船》、《家族》,苏童的“飞越枫杨树系列”,李佩甫的《李氏家族》,陈忠实的《白鹿原》,王旭烽的《南方有嘉木》,阿来的《尘埃落定》,李锐的《旧址》、《银城故事》,莫言的《丰乳肥臀》,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
请教个问题...关于暗潮的...
darkwave是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产生,主要和gothic,post-punk和new-wave音乐运动有关.."早期的黑浪潮亦是电子舞风颇浓,且如今电子音乐一直是Darkwave之重要组成部分.那么DIE FORM呢"早期的暗潮音乐是电子味比较浓,他们现在和EBM音乐也脱离不了暧昧的关系,因为他毕竟是和new-wave有关联,关于new-wave我不是很了解,但...
《红楼梦》有哪些文学价值?
全书中出现了400多个人物,以一个贵族家庭中的两个分支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充满人文主义精神。 2、俄国 19世纪80年代,瓦西里耶夫:《红楼梦》写得如此美妙,如此有趣,以致非得产生模仿者不可! 3、德国 1932年,库恩《红楼梦》德文节译本“后记”:这样一个关心精神文明的欧洲,怎么可能把《红楼梦》这样...
黑帮???
新的组织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由普洛文扎诺和绝对效忠他的6名“顾问”组成,这些顾问是黑手党内的“专家”,分别主管毒品走私、工程承包、财务及武装力量;第二层次是巴勒莫、阿格里琴托、卡塔尼塞塔等西部三省的黑手党强势家族的重量级人物;第三层次是西西里的所有黑手党家族。 经过一场“大反思”,黑手党放弃了“挑...
老班章纪事 | 老班章四大家族的由来
为了不让茶友们阅读时产生理解混乱,以区分新班章、老班章和班章村委会,所以本文通用“老班章”来叙事。 2、哈尼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因而拥有着庞大的支系,仅在西双版纳就有阿卡、僾尼等分支,其他地州的分支则为更多,所以为了简单叙事和减少茶友读者的阅读困难,本文统称哈尼族。四大家族是...
没书看了,推荐本吧!!
2.《穆斯林的葬礼》 作者:霍达 一个穆斯林的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宗教的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展现了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实垂涎。作品清新...
盗墓笔记中青铜门后面的终级到底是什么?
和外族女子通婚了,被家族驱赶出去,就出现了后来的一个分支,张家大佛爷的前身父辈们,张家大佛爷那个家族分出去以后,没有掌握长生不老术,但他的家族盗墓本领还是有的,之后张家大佛爷在“那个年代”进入了政界,三叔书中指的“那个年代”是让所有年轻人狂热的年代,这里不就露骨的表明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年代...
wave是什么的一种音乐类型?
Gangsta Rap是 Rap的一种,以 Rap的内容多与都市罪案有关,充满暴力、色欲感受,这是反映现实的一种音乐路向。 Gangsta Rap於八十年代末期在美国兴起,音乐Rap中的强悍尖锐派,在美国大受欢迎,唱片销路甚高。而不少 Gangsta Rap乐手本身真正“参与”现实中各式罪案,部分更因而入狱甚至死亡,可说是真正反映现实兼令人...
《扫黑风暴》烂尾了吗
相比48集的《破冰行动》,《扫黑风暴》体量上要精简很多,只有28集,本该以叙事紧凑、信息密度大见长,可随着剧情推进,也暴露了和前者同样的问题。 这同内容的捉襟见肘分不开。因为正反派实在过于明显,许多谜团变得无处安放,只好在氛围上下功夫。比如李成阳的耳鸣,在馄饨店踯躅的画面出现了许多次,但这类画面没有信息...
黑帮电影与现实生活有多大差距?
此外,李子雄、曾江、徐锦江甚至出现不到两分钟的吴孟达,也都有着不错的发挥,将这样一部人物关系庞杂的电影演绎得扣人心弦。 可以说,《跛豪》讲述的是一个黑帮大佬、一个毒枭、一个家族领导者的故事。从某种角度看,这样一个人物并不光明,但全片看下来,你会对这样一个人物产生深刻印象,也会引发深刻思考。 最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