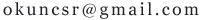当欧洲笼罩于基督教的黑暗之时,以伊斯兰为特征的阿拉伯帝国文明光芒璀璨,成就斐然。对于这种文明的地位,权威的科学史学家的评价是,纵向来看,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希腊、罗马)启后(文艺复兴)的作用;横向来看,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了解一些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西方学者曾广泛使用阿拉伯文,或受益于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文化,许多科学著作都是用阿拉伯语撰写的,帝国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因此,前西德历史学家赫伯特·格特沙尔克在《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一书中写到:“全世界都感谢阿拉伯语在传播中世纪高度发展的阿拉伯科学知识方面所带来的媒体作用……如果没有阿拉伯语这个媒介,得到这些知识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会了解得那么早。”
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西欧人对希腊知识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这一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恢复他们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古典著作的作用。”
而作者Robert Briffault在《构建人性》中则更加明确地说:“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现代的欧洲文明就根本不会出现,这是极其可能的;绝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他们,欧洲便不会扮演那么一种超越所有先前进步阶段角色。” “正是在阿拉伯与摩尔人文化的感召下……真正的文艺复兴才得以发生。正是西班牙而非意大利,成为欧洲再生的摇篮……”
居斯塔夫·勒朋旗帜鲜明地指出:“十字军战争不是导致学术进入欧洲的主要原因,而是通过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
他在《阿拉伯文明》一书中写道:“阿拉伯人迅速地创立了一种与以往的许多文化有着很大差异的新兴文明。由于他们良好的政策,使许多民族接受了他们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连具有古老文明的埃及人、印度人也不例外,他们情愿地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和建筑艺术……”
《西班牙的摩尔人》的作者、英国人斯坦利·莱恩·普尔说:“西班牙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近8个世纪里,发展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的光辉典范——当欧洲其它地方呈现萧条的时候,这个国度的艺术、文学与科学一片繁荣。来自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求学者聚集在这里,汲取这些流淌在摩尔人的城市里的知识的甘泉。”历史上,在西班牙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与格拉纳达的高等学府里,云集着为数众多的基督徒与犹太学生,他们如饥似渴地向穆斯林学者学习科学,然后又把所学到的知识在欧洲播散。以下引用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写给西班牙哈里发希沙姆三世(公元1027~1031年在位)的一封信函,他在信中请求允许派遣王族成员前往科尔多瓦大学学习。
“乔治二世——英国、高卢、瑞典及挪威的国王,致西班牙穆斯林国王哈里发希沙姆三世陛下:
我们已经获悉,贵国之科学、知识、技术与制造业甚为发达,故,鉴于我们的国家在此类方面之匮乏,及全然处于愚昧无知,我们希望获得良机,以使我们的青年人受益于贵方之成就。
我们期盼这种良机可以让我们跟随你们的脚步前进,并以知识照亮我们的人民。鄙侄女杜邦特公主及一些英国贵族女子,希望受惠于你们的学术机构(科尔多瓦大学——笔者注)。对您特许给予我们机会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致以敬意。
年轻的公主将为陛下晋献一份礼物。您若能够收下我们将倍感荣幸。
落款:您顺从的仆人,乔治”
西班牙穆斯林创建的大学也是后来一些欧洲早期的大学的模范,例如阿方索八世于公元1208年建立的帕伦西亚大学与弗雷德里克二世于公元1224年建立那不勒斯大学。
尽管基督教世界翻译穆斯林的科学著作在诸如巴塞罗纳、里昂或图卢兹等地进行,但是占据首要位置的无疑是西班牙的托莱多。这座从公元8世纪初至11世纪的3~4百年之间由摩尔人穆斯林治理的城市,开始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其声望尤其是在翻译工作大规模开展的12世纪以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托莱多被译成拉丁语的穆斯林科学著作应该有几百部以上。事实上,欧洲也因此而涌现出诸杰拉德、普拉托、阿德拉尔德、罗杰·贝肯、罗伯特·切斯特,以及荷尔曼等著名的翻译家。他们云集于此,如饥似渴地从事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在那些翻译家来到托莱多之前,那里甚至还出现了后来成为罗马教皇的吉伯特(公元940~1003年)的身影。]。《全球通史》也提到这些翻译家,它写到:“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来到托莱多的目的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获取穆斯林的科学知识。
自公元12世纪阿拉伯帝国学者的著作(和希腊、罗马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被大批译成拉丁语及其它欧洲语言以来,欧洲各大学将它们作为教科书长达几个世纪。
科学史告诉我们,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承前启后,独步中古。如果将《构建人性》加以引申,人们就会明确无误地看到,彼时其科学技术与文化水平代表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阿拉伯帝国文明在科学上多有建树,而且正是通过广大科学家与学者的创造性劳动,古代印度、希腊、波斯与罗马的科学巨著得以矫正并保存。
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从阿拉伯语书写的这些古代希腊与罗马巨著开始,点燃了复兴的火炬。如果没有崇尚科学的穆斯林的辛勤劳动,今天就不会有人看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了;因为中世纪笼罩在欧洲的基督教的黑暗几乎摧毁了一切古代希腊与罗马的科学文化典籍,尽管衰败的拜占廷可能剩下典籍中的片言只语。不要轻视阿拉伯帝国科学的作用——当苟延残喘的拜占廷几乎完全隔绝欧洲通向东方的道路之时,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经由当时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往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而奠定今日科学基础的文艺复兴,正是始于欧洲的这些地方。
对此,Arnold和Guillaume编撰的《伊斯兰的遗产》有所佐证。该书写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映射着希腊的光芒,当希腊科学的白昼流逝,伊斯兰(医学与)科学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最黑暗的夜晚……因为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指引或引导了那场伟大的运动(文艺复兴),所以我们有理由宣称这种文明依然与我们同在。”
流传下来阿拉伯帝国科学的历史文稿有时是很粗略的,这使得一些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它的科学只不过是对希腊科学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前的一种保存。出现这种错觉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科学著作几乎都是以阿拉伯语书写的,而今天的科学编年史学家真正精通这种科学语言的已经不多了。另外,一些被翻译成拉丁语或其它语言的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已然很难分辨它们的渊源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模糊”处理。
但是,一些史学家力图歪曲史实,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只不过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点余光。”其实,这种蓄意抹杀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地位与成就的鼓噪,不是处于无知,就是缘于偏见。而事实是足以胜过诡辩的。
诸如Otto Neugebauer与Delambre之类所谓的学者甚至走的更远。例如在他们的报告里,伊斯兰天文学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穆斯林也从来不曾凝视过星空,尽管那时的繁星也是像今天一样俯瞰着大地。而Pierre Duhem的态度则可谓是滑稽可笑了。按着他的逻辑,中世纪的穆斯林在天文学方面同时身兼两重身份――一是疯狂焚烧托勒密书稿的暴徒,二是毫无建树地模仿希腊科学的抄写员。可是,一个抄写员如何能够眷抄一部已经投进烈焰的书稿?这就好比让Duhem先生用自己的脚掌抽自己的嘴巴一样困难。此类荒唐的逻辑也不乏追随者,他们甚至企图使人类的天文学由托勒密直接蛙跳到哥白尼,而这一步蛙跳几乎有1500年的距离。先后担任国英国欧文学院与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陶特说:“看到还有人相信,一个人能够从伯里克利或奥古斯都时代一步蛙跳到美第奇和路易14时代,这实在令人痛心……从头开始固然好,但是我们根本不能随意在某个时候停下来,跳跃过数百年,然后重新开始。”
现在来戳穿一个关于穆斯林征服者焚毁亚力山大图书馆的寓言故事,以便使“疯狂焚烧托勒密书稿”这样的故事就此止步,也为让Duhem之类的“伪术士”在天真的读者面前被彻底揭去伪装的面皮。
居斯塔夫·勒朋的《阿拉伯文明》有这样一段文字:“所谓的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这样荒蛮的行为并不符合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道德准则。人们会产生这样的质疑――那些杰出的学者们长久以来怎么会相信这样一种传说?这种传说遭到我们这个时代唾弃,根本没有再去讨论必要了。没有什么事情比证明在伊斯兰征服世界以前,是基督徒自己焚毁了异教徒的书籍更容易了。”
奇怪的是,那些穆斯林征服时代或稍晚一些的、人才济济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人留下对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事件的片言只语的记载,倒是到了13世纪突然冒出3个人讲起这个故事,其中尤以一个人叫Ibnul al’Ibri(意思是“犹太人的儿子”)的说法经不起推敲。按照这位“犹太人的儿子”的说法,那些被焚烧的70万册书被亚力山大的4000座浴室当作燃料连续燃烧了半年的时间。但是,这种说法却出现了简单的算数问题――如果把按此人所说的70万册书分送到4000座浴室,那么每个浴室只能分到175本,而要想让这175本书连续焚烧半年,则每本书至少需要持续燃烧1天以上。况且多达70万册这一数量本身就是令人无法相信的。由此听众便有理由怀疑这个“犹太人的儿子”讲述的“寓言”故事的真实性了。事实上亚力山大图书馆倒真是被放了两次大火,一次在公元前48年,放火的是大名鼎鼎的朱利斯·恺撒的舰队,另一次在公元391年,适值罗马帝国狄奥多西统治时期。莫非“犹太人的儿子”以那两次放火为蓝本,杜撰了一个寓言故事?
约翰·威廉·德雷珀在《欧洲知识发展》一书中仗义执言说道:“欧洲文献故意系统性地抹杀穆斯林的科学成就,对此我不得不表示悲愤。但是我肯定,他们再也不会继续被隐瞒下去了。建立在宗教敌视与民族自负基础上的偏见永远都不会长久。”
在乔治·萨顿的《科学史导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些荣耀的名字足以让人们想起,在西方是没有同时代的人物能够与这些名字相匹敌的……加长由这些名字组成的豪华的名单也并不是困难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中世纪的科学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就把这些名字读给他听,他们所有人都是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内取得辉煌成就的——公元750~1100年。”
让我们回味一下乔治·萨顿的一句话的含义吧——“一个自以为是和虚伪的哲学家不可能理解伊斯兰的智慧,同样也应受到谴责。”
前文引用的文献作者皆为研究科学史的著名学者。另外,也有一些“大众化”人物所言亦可稽考。但愿这些政治家或政客不是不学无术、胡说八道。
《自然辩证法》一书指出:“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大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科学史的评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中说:“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西方音乐界及作曲界则忌讳“9”,因为贝多芬创作了举世闻名的9大交响曲后辞世。此后舒伯特、德沃夏克、威廉斯等名作曲家也都在写完9首交响曲后与世长辞。
有趣的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在写完八首交响乐,并为之编号后有意继续写,但又想逃过“9”字,就写了一首不编号的交响曲,果然安然无恙,但后来他又创作了一首交响乐,将之编号为9,不幸在尚未编写十号交响乐前就死了。
在日本,忌讳“9”字,是“9”的发音与“苦”相近
了解一些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西方学者曾广泛使用阿拉伯文,或受益于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文化,许多科学著作都是用阿拉伯语撰写的,帝国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因此,前西德历史学家赫伯特·格特沙尔克在《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一书中写到:“全世界都感谢阿拉伯语在传播中世纪高度发展的阿拉伯科学知识方面所带来的媒体作用……如果没有阿拉伯语这个媒介,得到这些知识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会了解得那么早。”
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西欧人对希腊知识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这一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恢复他们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古典著作的作用。”
而作者Robert Briffault在《构建人性》中则更加明确地说:“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现代的欧洲文明就根本不会出现,这是极其可能的;绝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他们,欧洲便不会扮演那么一种超越所有先前进步阶段角色。” “正是在阿拉伯与摩尔人文化的感召下……真正的文艺复兴才得以发生。正是西班牙而非意大利,成为欧洲再生的摇篮……”
居斯塔夫·勒朋旗帜鲜明地指出:“十字军战争不是导致学术进入欧洲的主要原因,而是通过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
他在《阿拉伯文明》一书中写道:“阿拉伯人迅速地创立了一种与以往的许多文化有着很大差异的新兴文明。由于他们良好的政策,使许多民族接受了他们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连具有古老文明的埃及人、印度人也不例外,他们情愿地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和建筑艺术……”
《西班牙的摩尔人》的作者、英国人斯坦利·莱恩·普尔说:“西班牙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近8个世纪里,发展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的光辉典范——当欧洲其它地方呈现萧条的时候,这个国度的艺术、文学与科学一片繁荣。来自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求学者聚集在这里,汲取这些流淌在摩尔人的城市里的知识的甘泉。”历史上,在西班牙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与格拉纳达的高等学府里,云集着为数众多的基督徒与犹太学生,他们如饥似渴地向穆斯林学者学习科学,然后又把所学到的知识在欧洲播散。以下引用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写给西班牙哈里发希沙姆三世(公元1027~1031年在位)的一封信函,他在信中请求允许派遣王族成员前往科尔多瓦大学学习。
“乔治二世——英国、高卢、瑞典及挪威的国王,致西班牙穆斯林国王哈里发希沙姆三世陛下:
我们已经获悉,贵国之科学、知识、技术与制造业甚为发达,故,鉴于我们的国家在此类方面之匮乏,及全然处于愚昧无知,我们希望获得良机,以使我们的青年人受益于贵方之成就。
我们期盼这种良机可以让我们跟随你们的脚步前进,并以知识照亮我们的人民。鄙侄女杜邦特公主及一些英国贵族女子,希望受惠于你们的学术机构(科尔多瓦大学——笔者注)。对您特许给予我们机会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致以敬意。
年轻的公主将为陛下晋献一份礼物。您若能够收下我们将倍感荣幸。
落款:您顺从的仆人,乔治”
西班牙穆斯林创建的大学也是后来一些欧洲早期的大学的模范,例如阿方索八世于公元1208年建立的帕伦西亚大学与弗雷德里克二世于公元1224年建立那不勒斯大学。
尽管基督教世界翻译穆斯林的科学著作在诸如巴塞罗纳、里昂或图卢兹等地进行,但是占据首要位置的无疑是西班牙的托莱多。这座从公元8世纪初至11世纪的3~4百年之间由摩尔人穆斯林治理的城市,开始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其声望尤其是在翻译工作大规模开展的12世纪以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托莱多被译成拉丁语的穆斯林科学著作应该有几百部以上。事实上,欧洲也因此而涌现出诸杰拉德、普拉托、阿德拉尔德、罗杰·贝肯、罗伯特·切斯特,以及荷尔曼等著名的翻译家。他们云集于此,如饥似渴地从事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在那些翻译家来到托莱多之前,那里甚至还出现了后来成为罗马教皇的吉伯特(公元940~1003年)的身影。]。《全球通史》也提到这些翻译家,它写到:“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来到托莱多的目的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获取穆斯林的科学知识。
自公元12世纪阿拉伯帝国学者的著作(和希腊、罗马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被大批译成拉丁语及其它欧洲语言以来,欧洲各大学将它们作为教科书长达几个世纪。
科学史告诉我们,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承前启后,独步中古。如果将《构建人性》加以引申,人们就会明确无误地看到,彼时其科学技术与文化水平代表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阿拉伯帝国文明在科学上多有建树,而且正是通过广大科学家与学者的创造性劳动,古代印度、希腊、波斯与罗马的科学巨著得以矫正并保存。
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从阿拉伯语书写的这些古代希腊与罗马巨著开始,点燃了复兴的火炬。如果没有崇尚科学的穆斯林的辛勤劳动,今天就不会有人看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了;因为中世纪笼罩在欧洲的基督教的黑暗几乎摧毁了一切古代希腊与罗马的科学文化典籍,尽管衰败的拜占廷可能剩下典籍中的片言只语。不要轻视阿拉伯帝国科学的作用——当苟延残喘的拜占廷几乎完全隔绝欧洲通向东方的道路之时,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经由当时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往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而奠定今日科学基础的文艺复兴,正是始于欧洲的这些地方。
对此,Arnold和Guillaume编撰的《伊斯兰的遗产》有所佐证。该书写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映射着希腊的光芒,当希腊科学的白昼流逝,伊斯兰(医学与)科学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最黑暗的夜晚……因为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指引或引导了那场伟大的运动(文艺复兴),所以我们有理由宣称这种文明依然与我们同在。”
流传下来阿拉伯帝国科学的历史文稿有时是很粗略的,这使得一些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它的科学只不过是对希腊科学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前的一种保存。出现这种错觉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科学著作几乎都是以阿拉伯语书写的,而今天的科学编年史学家真正精通这种科学语言的已经不多了。另外,一些被翻译成拉丁语或其它语言的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已然很难分辨它们的渊源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模糊”处理。
但是,一些史学家力图歪曲史实,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只不过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点余光。”其实,这种蓄意抹杀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地位与成就的鼓噪,不是处于无知,就是缘于偏见。而事实是足以胜过诡辩的。
诸如Otto Neugebauer与Delambre之类所谓的学者甚至走的更远。例如在他们的报告里,伊斯兰天文学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穆斯林也从来不曾凝视过星空,尽管那时的繁星也是像今天一样俯瞰着大地。而Pierre Duhem的态度则可谓是滑稽可笑了。按着他的逻辑,中世纪的穆斯林在天文学方面同时身兼两重身份――一是疯狂焚烧托勒密书稿的暴徒,二是毫无建树地模仿希腊科学的抄写员。可是,一个抄写员如何能够眷抄一部已经投进烈焰的书稿?这就好比让Duhem先生用自己的脚掌抽自己的嘴巴一样困难。此类荒唐的逻辑也不乏追随者,他们甚至企图使人类的天文学由托勒密直接蛙跳到哥白尼,而这一步蛙跳几乎有1500年的距离。先后担任国英国欧文学院与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陶特说:“看到还有人相信,一个人能够从伯里克利或奥古斯都时代一步蛙跳到美第奇和路易14时代,这实在令人痛心……从头开始固然好,但是我们根本不能随意在某个时候停下来,跳跃过数百年,然后重新开始。”
现在来戳穿一个关于穆斯林征服者焚毁亚力山大图书馆的寓言故事,以便使“疯狂焚烧托勒密书稿”这样的故事就此止步,也为让Duhem之类的“伪术士”在天真的读者面前被彻底揭去伪装的面皮。
居斯塔夫·勒朋的《阿拉伯文明》有这样一段文字:“所谓的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这样荒蛮的行为并不符合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道德准则。人们会产生这样的质疑――那些杰出的学者们长久以来怎么会相信这样一种传说?这种传说遭到我们这个时代唾弃,根本没有再去讨论必要了。没有什么事情比证明在伊斯兰征服世界以前,是基督徒自己焚毁了异教徒的书籍更容易了。”
奇怪的是,那些穆斯林征服时代或稍晚一些的、人才济济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人留下对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事件的片言只语的记载,倒是到了13世纪突然冒出3个人讲起这个故事,其中尤以一个人叫Ibnul al’Ibri(意思是“犹太人的儿子”)的说法经不起推敲。按照这位“犹太人的儿子”的说法,那些被焚烧的70万册书被亚力山大的4000座浴室当作燃料连续燃烧了半年的时间。但是,这种说法却出现了简单的算数问题――如果把按此人所说的70万册书分送到4000座浴室,那么每个浴室只能分到175本,而要想让这175本书连续焚烧半年,则每本书至少需要持续燃烧1天以上。况且多达70万册这一数量本身就是令人无法相信的。由此听众便有理由怀疑这个“犹太人的儿子”讲述的“寓言”故事的真实性了。事实上亚力山大图书馆倒真是被放了两次大火,一次在公元前48年,放火的是大名鼎鼎的朱利斯·恺撒的舰队,另一次在公元391年,适值罗马帝国狄奥多西统治时期。莫非“犹太人的儿子”以那两次放火为蓝本,杜撰了一个寓言故事?
约翰·威廉·德雷珀在《欧洲知识发展》一书中仗义执言说道:“欧洲文献故意系统性地抹杀穆斯林的科学成就,对此我不得不表示悲愤。但是我肯定,他们再也不会继续被隐瞒下去了。建立在宗教敌视与民族自负基础上的偏见永远都不会长久。”
在乔治·萨顿的《科学史导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些荣耀的名字足以让人们想起,在西方是没有同时代的人物能够与这些名字相匹敌的……加长由这些名字组成的豪华的名单也并不是困难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中世纪的科学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就把这些名字读给他听,他们所有人都是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内取得辉煌成就的——公元750~1100年。”
让我们回味一下乔治·萨顿的一句话的含义吧——“一个自以为是和虚伪的哲学家不可能理解伊斯兰的智慧,同样也应受到谴责。”
前文引用的文献作者皆为研究科学史的著名学者。另外,也有一些“大众化”人物所言亦可稽考。但愿这些政治家或政客不是不学无术、胡说八道。
《自然辩证法》一书指出:“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大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科学史的评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中说:“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西方音乐界及作曲界则忌讳“9”,因为贝多芬创作了举世闻名的9大交响曲后辞世。此后舒伯特、德沃夏克、威廉斯等名作曲家也都在写完9首交响曲后与世长辞。
有趣的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在写完八首交响乐,并为之编号后有意继续写,但又想逃过“9”字,就写了一首不编号的交响曲,果然安然无恙,但后来他又创作了一首交响乐,将之编号为9,不幸在尚未编写十号交响乐前就死了。
在日本,忌讳“9”字,是“9”的发音与“苦”相近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无其他回答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