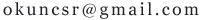1.《挪威森林》要是我现在把肩膀放松,会一下土崩瓦解的。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以后也只能这样活下去。一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我就会分崩离析——被一片片吹散到什么地方去。这点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说照顾我?一 个人度过的四月是个太过寂寞的季节。四月里,周围的人看起来都是很幸福。人们脱下大衣 ,在阳光下聊天,玩投球,谈情说爱,而我完全的孤苦零丁。直子,阿绿,永泽,。。。到了五月,我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在颤抖和摇动,那种颤动通常在黄昏时 刻来临。在木莲花香轻轻飘荡的昏暗中,我的心莫名地被膨胀,颤抖,摇晃和痛楚所刺痛。那时我就紧闭双眼,咬紧牙关,等候那种痛楚过去,它在漫长的时间里过 去以后,留下隐隐的痛楚。那女孩人不错,又喜欢同她睡觉.现在也不时有些怀念,但不知何故,就是不曾为之倾心.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 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但又总是怅然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而伤害了直子. 我扬起脸,望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我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 记忆这东西真有些不可思议.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十八年后仍历历在目.对那时的我来说,风景那玩艺儿是无所谓的.坦率地说,那时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只是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只是我与她的关系,而后又转回我自己.在那个年纪,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会像回镖一样转到自己手上.更何况我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纷纭而微妙的境地,根本不容我有欣赏周围风景的闲情逸致. 它们比往常更持久地,更有力地在我的头部猛踢不已:起来理解我!惟有如此,我才动笔写这些文字.我这人,无论对什么,都务必形诸文字,否则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 很久以前,当我还年轻,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我就几次有过写一下直子的念头,却连一行也未能写成.虽然我明白,只要写出第一行,往下就夫文思泉涌.但就是死活写不出那第一行.一切都清晰得历历在昨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处着手,就像一张十分详尽的地图, 有时反而因其过于详尽而不便于使用.但我现在明白:归根到底,我想,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并且发觉,关于直子的记忆越是模糊,我才愈能深入地了解她.时到今日,我才恍然大悟到直子只所以求我别忘掉她的原因.真子当然知道,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记忆迟早要被冲淡.惟其如此,她才强调说: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曾这样存在过. 想到这里,我就悲哀得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到我都感觉到不胜悲哀.那正是与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性质的悲哀.这种莫可名状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深藏于内.它就像掠身而过的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其语言却未能传入我的耳中. 一如往日的校园午休光景.然而在隔了许久后重新观望这光景的时间里,我葛然注意到一个事实:每个人无不显得幸福.至于他们是真的幸福还是仅仅从表面看上去如此,就无从得知了.但无论如何,在九月间那个令人心神荡漾的下午,每个人看起来都自得其乐.而我却因此而感受到了平时所没有感到过的孤寂,觉得惟独我自己与这光景格格不入. 它类似少年时代的一种憧憬,一种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我连它曾在我心里存在过都记不起来了.而初美所摇憾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当我恍然大悟时,一时悲怆之极,几欲涕零.她的确的的确确是位特殊的女性,无论如何都有人该向她伸出援救之手的.2.《寻羊冒险记》然而在两人认为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坏掉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已无可挽回。我们置身于被拉长了的平静的死胡同中。那是我们的尽头。” “对于她,我成了已然失却的人。” “为了重新找到业已失却的东西,他开始在酒精的迷雾中彷徨,状态每况愈下。” “我们到处卖弄空洞词句。跟你说,真诚的话语哪里都没有,如同哪里都没有真诚的呼吸。” “可能我开错了门却有后退不得。但不管怎样,既然门已打开,就只能进去。” “某种意义上,这里算是我的一个归宿。我觉得我似乎来到了应该来的地方,又好像逆所有河流来到了这里。对此我无法作出判断。” “哪里都不存在我的归宿。谁也不再想见到我,谁也不再需求我,谁也不希望被我需求。”3.《舞舞舞》明白。”我说,“那么我到底如何是好呢?”
“跳舞,”羊男说,“只要音乐在响,就尽管跳下去。明白我的话?跳舞!不停地
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艺儿本来就没有的。要是考
虑这个脚步势必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我就再也爱莫能助了。并且连接你的线索也将全
部消失,永远消失。那一来,你就只能在这里生存,只能不由自主地陷进这边的世界。
因此不能停住脚步,不管你觉得如何滑稽好笑,也不能半途而废,务必咬紧牙关踩着舞
点跳下去。跳着跳着,原先坚固的东西便会一点点疏软开来,有的东西还没有完全不可
救药。能用的全部用上去,全力以赴,不足为惧的。你的确很疲劳,精疲力竭,惶惶不
可终日。推都有这种时候,觉得一切都错得不可收拾,以致停下脚步。”
我抬起眼睛,再次凝视墙上的暗影。
“但只有跳下去,”羊男继续道,“而且要跳得出类拔萃,跳得大家心悦诚服。这
样,我才有可能助你一臂之力。总之一定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思考又发出回响。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善恶这一标准也已被仔细分化,被偷梁换柱。善之中有时髦的善和不时髦的善,恶之中有时髦的恶和不时髦的恶。时髦的善之中有正规的,有随便的,有温柔的,有冷漠的,有充满激情的,有装模作样的。其组合式也令人饶有兴味。如同米索尼毛衣配上尔萨尔迪裤子,脚穿波里尼皮鞋一样,可以享受复杂风格的乐趣。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
当时我没有在意,如今看来,1969年世界还算是单纯的。在某些场合,人们只消向机动队员扔几块石头便可以实现自我表现的愿望。时代真是好极了。而在这是非颠倒的哲学体系之下,究竟有谁能向警察投掷石块呢?有谁能够去主动迎着催泪弹挺身而上呢?这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处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这并非危言耸听。
记者全力以赴地揭露内幕。然而无论他怎样大声疾呼,其报道都莫名其妙地缺乏说服力,缺乏感染力,甚至越是大声疾呼越是如此。他不明白:那等事甚至算不上内幕,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程序。人们对此无不了然于心,因此谁也不去注意。巨额资本采用不正当手段猎取情报,收买土地,或强迫政府做出决定;而其下面,地痞无赖恫吓小本经营的鞋店,殴打境况�1�7j惶的小旅馆老板——有谁把这些放在心上呢?事情就是这样。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4.《奇鸟行状录》一个人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果真是可能的吗?也就是说,为了了解某某人而旷日持久地连续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其结果能使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触及对方的本质呢?我们对我们深以为了解的对象,难道真的知道其关键事情吗? “我们如此目睹的光景,不过是世界极小极小一部分。我们习惯上认为这便是世界的世界,其实并不是真的。真正的世界位于更深更暗的地方,大部分由水母这样的生物占领着,我们只是把这点给忘了。” 5.《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疗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手段。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艺。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里检查电冰箱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而那就是我。
“书那玩艺儿是煮细面条时用来打发时间才看的,明白?”
我读了米什莱的《魔女》。书写得不错,其中有这样一节:
“洛林地方法院的优秀法官莱米烧死了八百个魔女。而他对这种‘恐怖政治,仍引以为自豪。他说:‘由于我遍施正义,以致日前被捕的十人不待别人下手,便主动自缢身亡。’(筷田浩一郎译)”“由于我遍施正义”,这句话委实妙不可言。
“再也无须前思后想,一切岂非已然过往。”
汝等乃地中之盐。”
“?”
“倘盐失效,当取别物代之。”鼠如此说道。
“慷慨付出的,便是经常得到的。”
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哈特费尔德说,“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麻雀的脑髓而已。”
“墓很小,小得像高跟鞋的后跟,注意别看漏。”
这15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维艰,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是太轻而易举了。
我们的各种努力认识和被认识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出深度。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
“不过,到头来都是一死。”我试探着说道。
“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50年要活。这呀那呀地边想边活,说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5千年还辛苦得多。是吧?”
诚如所言。
鼠的小说有两个优点。一是没有性场面,二是一个人也没死。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
在别人家里醒来,我总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把别的魂灵硬是塞进别的体魄里似的。
酒吧里边,香烟味儿、威士忌味儿、炸马铃薯味儿.以及腋窝味儿下水道味儿.如同年轮状西餐点心那样重重叠叠地沉淀在一起。
她走掉之后,我的提问因没得到回答,仍在空中徘徊了一会儿。
“不过,我还真看了不少书哩,自从上次跟你聊过以后。你可知道《较之贫瘠的真实我更爱华丽的虚伪》?”
于是我又往那里打电话,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去哪里不晓得,便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是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空中开花,七零八落。常有的事,是不?”
“说家里人坏话,的确不大地道,心里不是滋味啊。”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时常狠狠捏住刮脸膏空盒落泪。”
“会意识到没有小拇指?”
“会的,戴手套的时候。”
“此外?”
她摇摇头。“说完全不会是撒谎。不过,也就是别的女孩意识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那种程度。”
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阳物为“你存在的理由”。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为主题写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归终没有完成,而我在那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我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整整生活了8个月之久。乘电车时先数乘客的人数,数楼梯的级数,一有时间就测量脉搏跳动的次数。据当时的记录,1969年8月15日至翌年4月3日之间,我听课358次,性交54次,吸烟6,921支。
那些日子里,我当真以为这种将一切换算成数值的做法也许能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然而无须说,任何人都不会对我吸烟的支数、所上楼梯的级数以及阳物的尺寸怀有半点兴致。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顾盼自怜。
因此,当我得知她的噩耗时,吸了第6,922支烟。
对鼠的父亲,我几乎一无所知,也没见过。我问过是何等人物,鼠答得倒也干脆:年纪远比他大,男性。
高中快毕业时,我决心把内心所想的事顶多说出一半。起因我忘了,总之好几年时间里我始终实践这一念头。并且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果真成了仅说一半话的人。
我并不知道这同冷静有何关系。但如果将一年到头都得除霜的旧式冰箱称为冷静的话,那么我也是这样。
庞大有时候会把事物的本质弄得面目全非。
“我一声不响地看着古坟,倾听风掠水面的声响。当时我体会到的心情,用语言绝对无法表达。不,那压根儿就不是心情,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完完全全被包围的感觉。就是说,蝉也罢蛙也罢蜘蛛也罢风也罢,统统融为一体在宇宙中漂流。”
那甲板的白漆由于潮风的侵蚀已变得红锈斑驳,船舷密密麻麻地沾满
贝壳,犹如病人身上脓疮愈后的硬疤。
好久没有感觉出夏日的气息了。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女孩肌体的感触,洗发香波的气味,傍晚的和风,缥缈的憧憬,以及夏日的梦境……”然而,这一切宛如一度揉过的复写纸,无不同原来有着少许然而却是无可挽回的差异。6.《且听风吟》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疗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手段。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艺。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里检查电冰箱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而那就是我。
“书那玩艺儿是煮细面条时用来打发时间才看的,明白?”
我读了米什莱的《魔女》。书写得不错,其中有这样一节:
“洛林地方法院的优秀法官莱米烧死了八百个魔女。而他对这种‘恐怖政治,仍引以为自豪。他说:‘由于我遍施正义,以致日前被捕的十人不待别人下手,便主动自缢身亡。’(筷田浩一郎译)”“由于我遍施正义”,这句话委实妙不可言。
“再也无须前思后想,一切岂非已然过往。”
汝等乃地中之盐。”
“?”
“倘盐失效,当取别物代之。”鼠如此说道。
“慷慨付出的,便是经常得到的。”
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哈特费尔德说,“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麻雀的脑髓而已。”
“墓很小,小得像高跟鞋的后跟,注意别看漏。”
这15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维艰,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是太轻而易举了。
我们的各种努力认识和被认识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出深度。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
“不过,到头来都是一死。”我试探着说道。
“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50年要活。这呀那呀地边想边活,说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5千年还辛苦得多。是吧?”
诚如所言。
鼠的小说有两个优点。一是没有性场面,二是一个人也没死。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
在别人家里醒来,我总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把别的魂灵硬是塞进别的体魄里似的。
酒吧里边,香烟味儿、威士忌味儿、炸马铃薯味儿.以及腋窝味儿下水道味儿.如同年轮状西餐点心那样重重叠叠地沉淀在一起。
她走掉之后,我的提问因没得到回答,仍在空中徘徊了一会儿。
“不过,我还真看了不少书哩,自从上次跟你聊过以后。你可知道《较之贫瘠的真实我更爱华丽的虚伪》?”
于是我又往那里打电话,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去哪里不晓得,便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是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空中开花,七零八落。常有的事,是不?”
“说家里人坏话,的确不大地道,心里不是滋味啊。”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时常狠狠捏住刮脸膏空盒落泪。”
“会意识到没有小拇指?”
“会的,戴手套的时候。”
“此外?”
她摇摇头。“说完全不会是撒谎。不过,也就是别的女孩意识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那种程度。”
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阳物为“你存在的理由”。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为主题写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归终没有完成,而我在那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我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整整生活了8个月之久。乘电车时先数乘客的人数,数楼梯的级数,一有时间就测量脉搏跳动的次数。据当时的记录,1969年8月15日至翌年4月3日之间,我听课358次,性交54次,吸烟6,921支。
那些日子里,我当真以为这种将一切换算成数值的做法也许能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然而无须说,任何人都不会对我吸烟的支数、所上楼梯的级数以及阳物的尺寸怀有半点兴致。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顾盼自怜。
因此,当我得知她的噩耗时,吸了第6,922支烟。
对鼠的父亲,我几乎一无所知,也没见过。我问过是何等人物,鼠答得倒也干脆:年纪远比他大,男性。
高中快毕业时,我决心把内心所想的事顶多说出一半。起因我忘了,总之好几年时间里我始终实践这一念头。并且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果真成了仅说一半话的人。
我并不知道这同冷静有何关系。但如果将一年到头都得除霜的旧式冰箱称为冷静的话,那么我也是这样。
庞大有时候会把事物的本质弄得面目全非。
“我一声不响地看着古坟,倾听风掠水面的声响。当时我体会到的心情,用语言绝对无法表达。不,那压根儿就不是心情,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完完全全被包围的感觉。就是说,蝉也罢蛙也罢蜘蛛也罢风也罢,统统融为一体在宇宙中漂流。”
那甲板的白漆由于潮风的侵蚀已变得红锈斑驳,船舷密密麻麻地沾满
贝壳,犹如病人身上脓疮愈后的硬疤。
好久没有感觉出夏日的气息了。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女孩肌体的感触,洗发香波的气味,傍晚的和风,缥缈的憧憬,以及夏日的梦境……”然而,这一切宛如一度揉过的复写纸,无不同原来有着少许然而却是无可挽回的差异。
“跳舞,”羊男说,“只要音乐在响,就尽管跳下去。明白我的话?跳舞!不停地
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艺儿本来就没有的。要是考
虑这个脚步势必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我就再也爱莫能助了。并且连接你的线索也将全
部消失,永远消失。那一来,你就只能在这里生存,只能不由自主地陷进这边的世界。
因此不能停住脚步,不管你觉得如何滑稽好笑,也不能半途而废,务必咬紧牙关踩着舞
点跳下去。跳着跳着,原先坚固的东西便会一点点疏软开来,有的东西还没有完全不可
救药。能用的全部用上去,全力以赴,不足为惧的。你的确很疲劳,精疲力竭,惶惶不
可终日。推都有这种时候,觉得一切都错得不可收拾,以致停下脚步。”
我抬起眼睛,再次凝视墙上的暗影。
“但只有跳下去,”羊男继续道,“而且要跳得出类拔萃,跳得大家心悦诚服。这
样,我才有可能助你一臂之力。总之一定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思考又发出回响。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善恶这一标准也已被仔细分化,被偷梁换柱。善之中有时髦的善和不时髦的善,恶之中有时髦的恶和不时髦的恶。时髦的善之中有正规的,有随便的,有温柔的,有冷漠的,有充满激情的,有装模作样的。其组合式也令人饶有兴味。如同米索尼毛衣配上尔萨尔迪裤子,脚穿波里尼皮鞋一样,可以享受复杂风格的乐趣。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
当时我没有在意,如今看来,1969年世界还算是单纯的。在某些场合,人们只消向机动队员扔几块石头便可以实现自我表现的愿望。时代真是好极了。而在这是非颠倒的哲学体系之下,究竟有谁能向警察投掷石块呢?有谁能够去主动迎着催泪弹挺身而上呢?这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处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这并非危言耸听。
记者全力以赴地揭露内幕。然而无论他怎样大声疾呼,其报道都莫名其妙地缺乏说服力,缺乏感染力,甚至越是大声疾呼越是如此。他不明白:那等事甚至算不上内幕,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程序。人们对此无不了然于心,因此谁也不去注意。巨额资本采用不正当手段猎取情报,收买土地,或强迫政府做出决定;而其下面,地痞无赖恫吓小本经营的鞋店,殴打境况�1�7j惶的小旅馆老板——有谁把这些放在心上呢?事情就是这样。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4.《奇鸟行状录》一个人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果真是可能的吗?也就是说,为了了解某某人而旷日持久地连续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其结果能使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触及对方的本质呢?我们对我们深以为了解的对象,难道真的知道其关键事情吗? “我们如此目睹的光景,不过是世界极小极小一部分。我们习惯上认为这便是世界的世界,其实并不是真的。真正的世界位于更深更暗的地方,大部分由水母这样的生物占领着,我们只是把这点给忘了。” 5.《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疗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手段。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艺。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里检查电冰箱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而那就是我。
“书那玩艺儿是煮细面条时用来打发时间才看的,明白?”
我读了米什莱的《魔女》。书写得不错,其中有这样一节:
“洛林地方法院的优秀法官莱米烧死了八百个魔女。而他对这种‘恐怖政治,仍引以为自豪。他说:‘由于我遍施正义,以致日前被捕的十人不待别人下手,便主动自缢身亡。’(筷田浩一郎译)”“由于我遍施正义”,这句话委实妙不可言。
“再也无须前思后想,一切岂非已然过往。”
汝等乃地中之盐。”
“?”
“倘盐失效,当取别物代之。”鼠如此说道。
“慷慨付出的,便是经常得到的。”
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哈特费尔德说,“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麻雀的脑髓而已。”
“墓很小,小得像高跟鞋的后跟,注意别看漏。”
这15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维艰,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是太轻而易举了。
我们的各种努力认识和被认识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出深度。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
“不过,到头来都是一死。”我试探着说道。
“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50年要活。这呀那呀地边想边活,说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5千年还辛苦得多。是吧?”
诚如所言。
鼠的小说有两个优点。一是没有性场面,二是一个人也没死。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
在别人家里醒来,我总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把别的魂灵硬是塞进别的体魄里似的。
酒吧里边,香烟味儿、威士忌味儿、炸马铃薯味儿.以及腋窝味儿下水道味儿.如同年轮状西餐点心那样重重叠叠地沉淀在一起。
她走掉之后,我的提问因没得到回答,仍在空中徘徊了一会儿。
“不过,我还真看了不少书哩,自从上次跟你聊过以后。你可知道《较之贫瘠的真实我更爱华丽的虚伪》?”
于是我又往那里打电话,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去哪里不晓得,便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是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空中开花,七零八落。常有的事,是不?”
“说家里人坏话,的确不大地道,心里不是滋味啊。”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时常狠狠捏住刮脸膏空盒落泪。”
“会意识到没有小拇指?”
“会的,戴手套的时候。”
“此外?”
她摇摇头。“说完全不会是撒谎。不过,也就是别的女孩意识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那种程度。”
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阳物为“你存在的理由”。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为主题写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归终没有完成,而我在那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我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整整生活了8个月之久。乘电车时先数乘客的人数,数楼梯的级数,一有时间就测量脉搏跳动的次数。据当时的记录,1969年8月15日至翌年4月3日之间,我听课358次,性交54次,吸烟6,921支。
那些日子里,我当真以为这种将一切换算成数值的做法也许能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然而无须说,任何人都不会对我吸烟的支数、所上楼梯的级数以及阳物的尺寸怀有半点兴致。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顾盼自怜。
因此,当我得知她的噩耗时,吸了第6,922支烟。
对鼠的父亲,我几乎一无所知,也没见过。我问过是何等人物,鼠答得倒也干脆:年纪远比他大,男性。
高中快毕业时,我决心把内心所想的事顶多说出一半。起因我忘了,总之好几年时间里我始终实践这一念头。并且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果真成了仅说一半话的人。
我并不知道这同冷静有何关系。但如果将一年到头都得除霜的旧式冰箱称为冷静的话,那么我也是这样。
庞大有时候会把事物的本质弄得面目全非。
“我一声不响地看着古坟,倾听风掠水面的声响。当时我体会到的心情,用语言绝对无法表达。不,那压根儿就不是心情,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完完全全被包围的感觉。就是说,蝉也罢蛙也罢蜘蛛也罢风也罢,统统融为一体在宇宙中漂流。”
那甲板的白漆由于潮风的侵蚀已变得红锈斑驳,船舷密密麻麻地沾满
贝壳,犹如病人身上脓疮愈后的硬疤。
好久没有感觉出夏日的气息了。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女孩肌体的感触,洗发香波的气味,傍晚的和风,缥缈的憧憬,以及夏日的梦境……”然而,这一切宛如一度揉过的复写纸,无不同原来有着少许然而却是无可挽回的差异。6.《且听风吟》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疗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手段。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艺。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里检查电冰箱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而那就是我。
“书那玩艺儿是煮细面条时用来打发时间才看的,明白?”
我读了米什莱的《魔女》。书写得不错,其中有这样一节:
“洛林地方法院的优秀法官莱米烧死了八百个魔女。而他对这种‘恐怖政治,仍引以为自豪。他说:‘由于我遍施正义,以致日前被捕的十人不待别人下手,便主动自缢身亡。’(筷田浩一郎译)”“由于我遍施正义”,这句话委实妙不可言。
“再也无须前思后想,一切岂非已然过往。”
汝等乃地中之盐。”
“?”
“倘盐失效,当取别物代之。”鼠如此说道。
“慷慨付出的,便是经常得到的。”
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哈特费尔德说,“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麻雀的脑髓而已。”
“墓很小,小得像高跟鞋的后跟,注意别看漏。”
这15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维艰,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是太轻而易举了。
我们的各种努力认识和被认识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出深度。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
“不过,到头来都是一死。”我试探着说道。
“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50年要活。这呀那呀地边想边活,说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5千年还辛苦得多。是吧?”
诚如所言。
鼠的小说有两个优点。一是没有性场面,二是一个人也没死。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
在别人家里醒来,我总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把别的魂灵硬是塞进别的体魄里似的。
酒吧里边,香烟味儿、威士忌味儿、炸马铃薯味儿.以及腋窝味儿下水道味儿.如同年轮状西餐点心那样重重叠叠地沉淀在一起。
她走掉之后,我的提问因没得到回答,仍在空中徘徊了一会儿。
“不过,我还真看了不少书哩,自从上次跟你聊过以后。你可知道《较之贫瘠的真实我更爱华丽的虚伪》?”
于是我又往那里打电话,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去哪里不晓得,便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是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空中开花,七零八落。常有的事,是不?”
“说家里人坏话,的确不大地道,心里不是滋味啊。”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时常狠狠捏住刮脸膏空盒落泪。”
“会意识到没有小拇指?”
“会的,戴手套的时候。”
“此外?”
她摇摇头。“说完全不会是撒谎。不过,也就是别的女孩意识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那种程度。”
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阳物为“你存在的理由”。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为主题写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归终没有完成,而我在那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我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整整生活了8个月之久。乘电车时先数乘客的人数,数楼梯的级数,一有时间就测量脉搏跳动的次数。据当时的记录,1969年8月15日至翌年4月3日之间,我听课358次,性交54次,吸烟6,921支。
那些日子里,我当真以为这种将一切换算成数值的做法也许能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然而无须说,任何人都不会对我吸烟的支数、所上楼梯的级数以及阳物的尺寸怀有半点兴致。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顾盼自怜。
因此,当我得知她的噩耗时,吸了第6,922支烟。
对鼠的父亲,我几乎一无所知,也没见过。我问过是何等人物,鼠答得倒也干脆:年纪远比他大,男性。
高中快毕业时,我决心把内心所想的事顶多说出一半。起因我忘了,总之好几年时间里我始终实践这一念头。并且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果真成了仅说一半话的人。
我并不知道这同冷静有何关系。但如果将一年到头都得除霜的旧式冰箱称为冷静的话,那么我也是这样。
庞大有时候会把事物的本质弄得面目全非。
“我一声不响地看着古坟,倾听风掠水面的声响。当时我体会到的心情,用语言绝对无法表达。不,那压根儿就不是心情,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完完全全被包围的感觉。就是说,蝉也罢蛙也罢蜘蛛也罢风也罢,统统融为一体在宇宙中漂流。”
那甲板的白漆由于潮风的侵蚀已变得红锈斑驳,船舷密密麻麻地沾满
贝壳,犹如病人身上脓疮愈后的硬疤。
好久没有感觉出夏日的气息了。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女孩肌体的感触,洗发香波的气味,傍晚的和风,缥缈的憧憬,以及夏日的梦境……”然而,这一切宛如一度揉过的复写纸,无不同原来有着少许然而却是无可挽回的差异。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3-08-18
他想把胸中的感念告诉对方:我们的心不是石头。石头也迟早会粉身碎骨,面目全非。但心不会崩毁。对于那种无形的东西—无论善还是恶—我们完全可以互相传达。
—《神的孩子全跳舞》 村上春树
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出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舞 舞 舞》村上春树
在某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要伤害另一个人。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村上春树
山川寂寥,街市井然,居民相安无事。可惜人无身影,无记忆,无心。男女可以相亲却不能相爱。爱须有心,而心已被嵌入无数的独角兽头盖骨化为“古老的梦”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作品小说语录经典语句名言
世上有可以挽回的和不可挽回的事,而时间经过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事。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村上春树
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挪威的森林》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
若什么都不舍弃,便什么都不能获取。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去的过程。
世上有可以挽回的和不可挽回的事,而时间经过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事。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山川寂寥,街市井然,居民相安无事。可惜人无身影,无记忆,无心。男女可以相亲却不能相爱。爱须有心,而心已被嵌入无数的独角兽头盖骨化为“古老的梦”。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挪威的森林》
一旦死去,就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这就是死亡的起点。
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出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舞、舞、舞》
世界上有什么不会失去的东西吗?我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
如果不了解而过得去,那再好不过了。
——《失落的弹珠玩具》
如果你想追求的是艺术或文学的话,只要去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就好了。
所谓完美的文章并不存在,就像完美的绝望不存在一样。
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任何人都想活得冷静。
——《风的歌》
若什么都不舍弃,便什么都不能获取。
那里的一切一切都如云遮雾绕一般迷离。但我可以感觉出那片风景中潜藏着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什么,而且我清楚:她也在看同样的风景。
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来的路时,所看到的仍似乎只是依稀莫辩的“或许”。我们所能明确认知的仅仅是现在这一瞬间,而这也只是与我们擦间而过。
纵令听其自然,世事的长河也还是要流往其应流的方向,而即使再竭尽人力,该受伤害的人也无由幸免。
迟早要失去的东西并没有太多意义。
必失之物的荣光并非真正的荣光。
刚刚好,看到你幸福的样子,于是幸福着你的幸福。
尽管世界上有那般广阔的空间
而容纳你的空间
——虽然只需一点点
——却无处可寻
因为没有人可以理解
因为没有人可以包容
因为没有人可以安慰……
所以才会让人有无处可去的感觉,就是说躯壳可以找到地方安置,可是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真正的容下你这个完完整整、纯洁的灵魂!!!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神的孩子全跳舞》 村上春树
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出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舞 舞 舞》村上春树
在某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要伤害另一个人。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村上春树
山川寂寥,街市井然,居民相安无事。可惜人无身影,无记忆,无心。男女可以相亲却不能相爱。爱须有心,而心已被嵌入无数的独角兽头盖骨化为“古老的梦”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作品小说语录经典语句名言
世上有可以挽回的和不可挽回的事,而时间经过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事。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村上春树
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挪威的森林》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
若什么都不舍弃,便什么都不能获取。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去的过程。
世上有可以挽回的和不可挽回的事,而时间经过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事。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山川寂寥,街市井然,居民相安无事。可惜人无身影,无记忆,无心。男女可以相亲却不能相爱。爱须有心,而心已被嵌入无数的独角兽头盖骨化为“古老的梦”。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挪威的森林》
一旦死去,就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这就是死亡的起点。
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出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舞、舞、舞》
世界上有什么不会失去的东西吗?我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
如果不了解而过得去,那再好不过了。
——《失落的弹珠玩具》
如果你想追求的是艺术或文学的话,只要去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就好了。
所谓完美的文章并不存在,就像完美的绝望不存在一样。
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任何人都想活得冷静。
——《风的歌》
若什么都不舍弃,便什么都不能获取。
那里的一切一切都如云遮雾绕一般迷离。但我可以感觉出那片风景中潜藏着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什么,而且我清楚:她也在看同样的风景。
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来的路时,所看到的仍似乎只是依稀莫辩的“或许”。我们所能明确认知的仅仅是现在这一瞬间,而这也只是与我们擦间而过。
纵令听其自然,世事的长河也还是要流往其应流的方向,而即使再竭尽人力,该受伤害的人也无由幸免。
迟早要失去的东西并没有太多意义。
必失之物的荣光并非真正的荣光。
刚刚好,看到你幸福的样子,于是幸福着你的幸福。
尽管世界上有那般广阔的空间
而容纳你的空间
——虽然只需一点点
——却无处可寻
因为没有人可以理解
因为没有人可以包容
因为没有人可以安慰……
所以才会让人有无处可去的感觉,就是说躯壳可以找到地方安置,可是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真正的容下你这个完完整整、纯洁的灵魂!!!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3-08-18
十八年的岁月如过眼烟云。往事历历,至今,我仍然能把那个大草原的景色清晰地描绘出来:霪雨绵绵把夏日洗涤得一尘不染,山坡浮动着嫩绿的绿浪,十月的软风,摇曳着稗草长穗,细长的云朵凝固了一般散部在碧蓝的清澈的浩空之中,天是那样的高,以至于把我的眼睛都看痛了。轻风掠过草原,吹开她的秀发,有飞翔杂树林中。树叶沙沙作响,间或传来远方的犬吠,那吠声如同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听起来,那样小,那样朦胧,再没有其他任何声音,没有其他任何人影。-------挪威的森林 我不能抛弃心,我想。无论它多么沉重,有时是多么黑暗,但它还是可以时而像鸟一样在风中漫舞,可以眺望永恒。我甚至可以使自己的心潜入这小小手风琴的声音之中。-------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海潮的清香,拍案的涛声,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在遥远的地方。"你是我的母亲吗?"我终于问道。"答案你早已知晓。"佐伯说。-------海边的卡夫卡 现在我们也都还各自活着,我想。无论失掉的多么致命,无论手中被夺去的多么宝贵,也无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而仅仅剩下一层表皮,我们都能这样没没无闻地打发人生,都能伸手拽过额定的时间将其送往身后——作为日常性的重复作业有时还会做得十分快捷。如此想着,我心里仿佛现出一个巨大的空洞。-------斯铺特尼克恋人 如今的我几乎没有称之为心的东西留下来。我的体温已遁往遥远的地方,有时我甚至不记得曾有过的体温。但我总还算可以哭泣。我实在孤苦难耐。我所在的是世界上最寒冷最孤寂的场所。每次哭时,冰男便吻我的脸颊。于是我的眼泪变成冰粒。他将这泪之冰粒拿在手中,放在舌头上。嗯,他说,我爱你。这不是说谎,我也心中有数,冰男确实爱我。不料一股不知何处吹来的风,将他冻得白晶晶的话语不断向过去、向过去吹去。我哭了,冰泪涟涟而下,在这遥远而寒冷的南极,在冰的家中。-------冰男 世界上有什么不会失去的东西吗?我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失落的弹珠玩具 一旦死去,就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这就是死亡的起点。-------舞、舞、舞 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去的过程-------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在某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要伤害另一个人。-------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世上有可以挽回的和不可挽回的事,而时间经过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事。-------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舞·舞·舞 于是我关闭我的语言,关闭我的心,深沈的悲哀是连眼泪这形式都无法采取的东西。-------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挪威的森林 对我来书,人生在20岁时就已终止了。后面的人生不过是绵延不断的后日谈而已,好比哪里也通不出去的弯弯曲曲若明若暗的长廊。然而我必须延续那样的人生。无非日复一日接受空虚的每一天又把它原封不动地送出去。-------海边的卡夫卡 “希望你记住我。”佐伯说,“只要有你记住我,被其他所有人忘掉都无所谓。”-------海边的卡夫卡 我一个人坐在檐廊里眼望院子。初夏的黄昏时分,树影长长的。家里仅我自己。我知道自己已被抛弃,孤零零地剩留下来。-------海边的卡夫卡
房间里一片岑寂。脑海如冬日夜空般历历分明,北斗七星和北极星在固定位置闪烁其辉。她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写,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要说。
-------斯普特尼克恋人“我满满一脑袋想写的东西,像个莫名其妙的仓库似的。”堇说,“各种各样的图像和场景、断断续续的话语、男男女女的身影——它们在我脑袋里时,全都活龙活现、闪闪生辉。我听见它们喝令我‘写下来!’而我也觉得能产生美妙的故事,能到达一个新的境地。可是一旦对着桌子写成文字,我就知道那宝贵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水晶没有结晶,而作为石块寿终正寝了。我哪里也去不成。”
-------斯普特尼克恋人“我想象远处有个小镇,小镇上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里有我真正的家人。房子不大,很朴素,但令人心里舒坦。在那里我可以同大家自然而然地心心相印,可以将所思所感毫无保留地说出口来。一到傍晚厨房就传来母亲做饭的动静,飘来暖融融香喷喷的饭味。那是本来的我应该在的地方。我总在脑海中描绘那个地方,让自己融入其中。”
-------斯普特尼克恋人
每个人都有只能在某个特殊年代得到的特殊东西。它好比微弱的火苗,幸运的人小心翼翼地呵护它助长它,使之作为松明燃烧下去。然而一旦失去,火苗便永远无法找回。我失去的不仅仅是堇,连那珍贵的火焰也随她一同失去了。
-------斯普特尼克恋人
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我思忖着,为什么非如此孤独不可呢?这个世界上生息的芸芸众生无不在他人身上寻求什么,结果我们却又如此孤立无助,这是为什么?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斯普特尼克恋人我闭上眼睛,竖起耳朵,推想将地球引力作为唯一纽带持续划过天空的斯普特尼克后裔们。它们作为孤独的金属块在畅通无阻的宇宙黑暗中偶然相遇、失之交臂、永离永别,无交流的话语,无相期的承诺。
-------斯普特尼克恋人
房间里一片岑寂。脑海如冬日夜空般历历分明,北斗七星和北极星在固定位置闪烁其辉。她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写,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要说。
-------斯普特尼克恋人“我满满一脑袋想写的东西,像个莫名其妙的仓库似的。”堇说,“各种各样的图像和场景、断断续续的话语、男男女女的身影——它们在我脑袋里时,全都活龙活现、闪闪生辉。我听见它们喝令我‘写下来!’而我也觉得能产生美妙的故事,能到达一个新的境地。可是一旦对着桌子写成文字,我就知道那宝贵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水晶没有结晶,而作为石块寿终正寝了。我哪里也去不成。”
-------斯普特尼克恋人“我想象远处有个小镇,小镇上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里有我真正的家人。房子不大,很朴素,但令人心里舒坦。在那里我可以同大家自然而然地心心相印,可以将所思所感毫无保留地说出口来。一到傍晚厨房就传来母亲做饭的动静,飘来暖融融香喷喷的饭味。那是本来的我应该在的地方。我总在脑海中描绘那个地方,让自己融入其中。”
-------斯普特尼克恋人
每个人都有只能在某个特殊年代得到的特殊东西。它好比微弱的火苗,幸运的人小心翼翼地呵护它助长它,使之作为松明燃烧下去。然而一旦失去,火苗便永远无法找回。我失去的不仅仅是堇,连那珍贵的火焰也随她一同失去了。
-------斯普特尼克恋人
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我思忖着,为什么非如此孤独不可呢?这个世界上生息的芸芸众生无不在他人身上寻求什么,结果我们却又如此孤立无助,这是为什么?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斯普特尼克恋人我闭上眼睛,竖起耳朵,推想将地球引力作为唯一纽带持续划过天空的斯普特尼克后裔们。它们作为孤独的金属块在畅通无阻的宇宙黑暗中偶然相遇、失之交臂、永离永别,无交流的话语,无相期的承诺。
-------斯普特尼克恋人
第3个回答 2020-04-11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