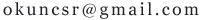回帖 更多守护秋雨吧
设置精华贴取消完成

打开贴吧APP,随时随地开启逗比模式
立即打开
孙光萱为什么报复余秋雨

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即金牙齿孙光萱),比较奇怪。不知有什么背景,不便多问,他也独来独往,行迹匆匆。那天中午见他匆匆从校门外进来,我们点过头正要让路,他却站下了,说:“我全见到他们了!”“见到谁呀?”大家问。“工总司的司令们。他们的学习会,我给他们讲鲁迅,他们都叫我老师。”他说。“他们也听鲁迅?”大家奇怪极了。因为当时在一般大学教师眼里,工总司的司令们大多是没有文化的混子。“他们还问我了,鲁迅抽什么烟?”他说。我们等他说下去。“亏得我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过,就立即告诉他们,青鸟牌。”他一笑,露出两颗发出铜绿的金牙齿。他的神情使我一哆嗦,立即下了一个决心,从此不再理他。因为,我爸爸的灾难,我全家的灾难,都来自工总司。我走开后还是郁愤难平。当时年轻气盛,总觉得应该治他一治,为他那“青鸟牌”。当天下午,根据我的谋划,我与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等几位演了一出恶作剧。我先叫邓琴芳故意哑着嗓子打一个电话进来,找他,说外地有人来咨询重大课题,学校工宣队郑重推荐由他来接待和回答。“学校工宣队怎么会知道我?”他显然十分兴奋。“可能是市里的工总司打了招呼。”邓琴芳说。过了一会儿,夏志明戴了帽子、眼镜和口罩,披了一件军大衣出现在他面前。握了一下手,也不寒暄,从大衣口袋里摸出—张由我拟写的纸条开始读问题:“鲁迅一共曾提到过五种狗:哈巴狗、叭儿狗、癞皮狗、落水狗、乏走狗。请问,这五种狗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他一听有点懵,嘴里嘀咕着:“哈巴狗、叭儿狗……”夏志明心太急,也许是怕露馅,又把我下面的问题一口气读了出来“再请问,叭儿狗是不是哈巴狗的儿子?还要问,是不是乏走狗实在走乏了,腿一软成了落水狗?另一个问题是,癞皮狗的皮,今后还能不能做狗皮膏药?……”这联珠炮似的荒诞问题使他眼睛睁得很大,而且很快就警觉了。他站起来,围着夏志明走了一圈,便干笑两声。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门外偷听,这下就哄然大笑了。但他却收住了干笑,冲着夏志明说:“这些问题,不是你想得出来的。”然后快速地扫了我一眼,气鼓鼓地走了。我当时没有预感,他会用多长的时间来报复我。只感到,连这种恶作剧也是无聊。哪儿都无聊,怎么都无聊,因此,只想天天回家与外公聊天。
(摘自余秋雨著《借我一生》)

设置精华贴取消完成

打开贴吧APP,随时随地开启逗比模式
立即打开
孙光萱为什么报复余秋雨

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即金牙齿孙光萱),比较奇怪。不知有什么背景,不便多问,他也独来独往,行迹匆匆。那天中午见他匆匆从校门外进来,我们点过头正要让路,他却站下了,说:“我全见到他们了!”“见到谁呀?”大家问。“工总司的司令们。他们的学习会,我给他们讲鲁迅,他们都叫我老师。”他说。“他们也听鲁迅?”大家奇怪极了。因为当时在一般大学教师眼里,工总司的司令们大多是没有文化的混子。“他们还问我了,鲁迅抽什么烟?”他说。我们等他说下去。“亏得我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过,就立即告诉他们,青鸟牌。”他一笑,露出两颗发出铜绿的金牙齿。他的神情使我一哆嗦,立即下了一个决心,从此不再理他。因为,我爸爸的灾难,我全家的灾难,都来自工总司。我走开后还是郁愤难平。当时年轻气盛,总觉得应该治他一治,为他那“青鸟牌”。当天下午,根据我的谋划,我与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等几位演了一出恶作剧。我先叫邓琴芳故意哑着嗓子打一个电话进来,找他,说外地有人来咨询重大课题,学校工宣队郑重推荐由他来接待和回答。“学校工宣队怎么会知道我?”他显然十分兴奋。“可能是市里的工总司打了招呼。”邓琴芳说。过了一会儿,夏志明戴了帽子、眼镜和口罩,披了一件军大衣出现在他面前。握了一下手,也不寒暄,从大衣口袋里摸出—张由我拟写的纸条开始读问题:“鲁迅一共曾提到过五种狗:哈巴狗、叭儿狗、癞皮狗、落水狗、乏走狗。请问,这五种狗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他一听有点懵,嘴里嘀咕着:“哈巴狗、叭儿狗……”夏志明心太急,也许是怕露馅,又把我下面的问题一口气读了出来“再请问,叭儿狗是不是哈巴狗的儿子?还要问,是不是乏走狗实在走乏了,腿一软成了落水狗?另一个问题是,癞皮狗的皮,今后还能不能做狗皮膏药?……”这联珠炮似的荒诞问题使他眼睛睁得很大,而且很快就警觉了。他站起来,围着夏志明走了一圈,便干笑两声。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门外偷听,这下就哄然大笑了。但他却收住了干笑,冲着夏志明说:“这些问题,不是你想得出来的。”然后快速地扫了我一眼,气鼓鼓地走了。我当时没有预感,他会用多长的时间来报复我。只感到,连这种恶作剧也是无聊。哪儿都无聊,怎么都无聊,因此,只想天天回家与外公聊天。
(摘自余秋雨著《借我一生》)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3-05-24
什么人一旦在一个行业产生竞争,肯定会结识恩怨的
第2个回答 2013-05-24
孙光萱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的这篇文章,虽本意不在揭露而在纠错,但实际上却让人们看到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一部分极为关键的真相,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对于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历史,余秋雨是怎样大胆地掩饰、改写、美化。由于余秋雨的叫板而引出的孙光萱的文章,等于把余秋雨逼到了墙角。不作任何回答,那等于是在默认。但要就具体问题反驳孙光萱,却又实在困难。于是余秋雨只得把面对批评时一再使用过的法宝再使用一回,即把孙光萱的动机归结为想出名,并且宣称“这种企图出名的强烈愿望使他的证言失去了公信力”。坦率地说,在继沙叶新之后,孙光萱又被余秋雨指控为想出名时,我感到了余秋雨的无奈,更感到了余秋雨的无聊。
孙光萱由此成为余秋雨最害怕也最痛恨的人。他在答北京《华夏时报》记者问时,含沙射影地把我和孙光萱比作“两个老纳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徐虹问“官司有无可能庭外调解”时说:“只有一个条件:古远清向法院揭发出向他提供那些诽谤材料的背后人物。然后,再由他来起诉那个造谣者,我有可能与古远清庭外调解”。
这里说的“那个提供材料者”,就是指孙光萱。孙光萱提供的材料,均是清查报告。说孙氏“诽谤”,其矛头是指向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班清查小组。正因为孙氏给我提供过材料,故在某种意义上说,告我就是告孙光萱,或告我就是为了恐吓孙光萱,以遏制孙光萱再披露真相,好让他从此闭嘴。
但孙光萱并没有被吓倒,他除为我提供证言,并无偿地提供了相当于给余“文革”错误作结论的夏其言致《新民周刊》的抗议信以及众多《清查报告》给我作证据外,还在官司期间写了《从“石一歌”谈到余秋雨》、《夏其言批评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不同的是,他的文章温柔敦厚,哪怕余一再攻击他乃至捏造各种罪名羞辱他,他均能正确对待,不以牙还牙。有人认为他患得患失太软弱,像余不止一次从人格上毁损他,碰到别人早就应战了。可他有自己做人和处事的原则:做老实人,决不说假话;以诚待人,决不做对不起历史、读者的事,决不趋炎附势。这样一来,“书生气”的确很重,开始他也是想真心挽救余,但余把他逼急了,也会豁出去的,他不怕恐吓之类的邪门歪道。他写的传诵一时的《正视历史,轻装前进》发表后,上海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写信称赞他的文章是“关于余秋雨现象讨论中最客观、最有说服力的。写这样的文章既要有阅历、见识,又要有勇气。”
这位上海作协副主席的话代表了广大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的心声。难怪上海作协换届选举理事时,余秋雨竟名落孙山。按他的知名度,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或副主席是当之无愧的。可广大作协会员就是不投他的票。他未当上理事后,据唐羽在《余秋雨很想看这本书》中说:余秋雨从此竟反常地把由上海作协主办按期赠送他的《上海文学》、《萌芽》杂志原封不动地退还,由此可看出他的气量之小。 孙光萱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的这篇文章,虽本意不在揭露而在纠错,但实际上却让人们看到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一部分极为关键的真相,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对于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历史,余秋雨是怎样大胆地掩饰、改写、美化。由于余秋雨的叫板而引出的孙光萱的文章,等于把余秋雨逼到了墙角。不作任何回答,那等于是在默认。但要就具体问题反驳孙光萱,却又实在困难。于是余秋雨只得把面对批评时一再使用过的法宝再使用一回,即把孙光萱的动机归结为想出名,并且宣称“这种企图出名的强烈愿望使他的证言失去了公信力”。坦率地说,在继沙叶新之后,孙光萱又被余秋雨指控为想出名时,我感到了余秋雨的无奈,更感到了余秋雨的无聊。
孙光萱由此成为余秋雨最害怕也最痛恨的人。他在答北京《华夏时报》记者问时,含沙射影地把我和孙光萱比作“两个老纳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徐虹问“官司有无可能庭外调解”时说:“只有一个条件:古远清向法院揭发出向他提供那些诽谤材料的背后人物。然后,再由他来起诉那个造谣者,我有可能与古远清庭外调解”。
这里说的“那个提供材料者”,就是指孙光萱。孙光萱提供的材料,均是清查报告。说孙氏“诽谤”,其矛头是指向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班清查小组。正因为孙氏给我提供过材料,故在某种意义上说,告我就是告孙光萱,或告我就是为了恐吓孙光萱,以遏制孙光萱再披露真相,好让他从此闭嘴。
但孙光萱并没有被吓倒,他除为我提供证言,并无偿地提供了相当于给余“文革”错误作结论的夏其言致《新民周刊》的抗议信以及众多《清查报告》给我作证据外,还在官司期间写了《从“石一歌”谈到余秋雨》、《夏其言批评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不同的是,他的文章温柔敦厚,哪怕余一再攻击他乃至捏造各种罪名羞辱他,他均能正确对待,不以牙还牙。有人认为他患得患失太软弱,像余不止一次从人格上毁损他,碰到别人早就应战了。可他有自己做人和处事的原则:做老实人,决不说假话;以诚待人,决不做对不起历史、读者的事,决不趋炎附势。这样一来,“书生气”的确很重,开始他也是想真心挽救余,但余把他逼急了,也会豁出去的,他不怕恐吓之类的邪门歪道。他写的传诵一时的《正视历史,轻装前进》发表后,上海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写信称赞他的文章是“关于余秋雨现象讨论中最客观、最有说服力的。写这样的文章既要有阅历、见识,又要有勇气。”
这位上海作协副主席的话代表了广大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的心声。难怪上海作协换届选举理事时,余秋雨竟名落孙山。按他的知名度,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或副主席是当之无愧的。可广大作协会员就是不投他的票。他未当上理事后,据唐羽在《余秋雨很想看这本书》中说:余秋雨从此竟反常地把由上海作协主办按期赠送他的《上海文学》、《萌芽》杂志原封不动地退还,由此可看出他的气量之小。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孙光萱由此成为余秋雨最害怕也最痛恨的人。他在答北京《华夏时报》记者问时,含沙射影地把我和孙光萱比作“两个老纳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徐虹问“官司有无可能庭外调解”时说:“只有一个条件:古远清向法院揭发出向他提供那些诽谤材料的背后人物。然后,再由他来起诉那个造谣者,我有可能与古远清庭外调解”。
这里说的“那个提供材料者”,就是指孙光萱。孙光萱提供的材料,均是清查报告。说孙氏“诽谤”,其矛头是指向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班清查小组。正因为孙氏给我提供过材料,故在某种意义上说,告我就是告孙光萱,或告我就是为了恐吓孙光萱,以遏制孙光萱再披露真相,好让他从此闭嘴。
但孙光萱并没有被吓倒,他除为我提供证言,并无偿地提供了相当于给余“文革”错误作结论的夏其言致《新民周刊》的抗议信以及众多《清查报告》给我作证据外,还在官司期间写了《从“石一歌”谈到余秋雨》、《夏其言批评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不同的是,他的文章温柔敦厚,哪怕余一再攻击他乃至捏造各种罪名羞辱他,他均能正确对待,不以牙还牙。有人认为他患得患失太软弱,像余不止一次从人格上毁损他,碰到别人早就应战了。可他有自己做人和处事的原则:做老实人,决不说假话;以诚待人,决不做对不起历史、读者的事,决不趋炎附势。这样一来,“书生气”的确很重,开始他也是想真心挽救余,但余把他逼急了,也会豁出去的,他不怕恐吓之类的邪门歪道。他写的传诵一时的《正视历史,轻装前进》发表后,上海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写信称赞他的文章是“关于余秋雨现象讨论中最客观、最有说服力的。写这样的文章既要有阅历、见识,又要有勇气。”
这位上海作协副主席的话代表了广大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的心声。难怪上海作协换届选举理事时,余秋雨竟名落孙山。按他的知名度,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或副主席是当之无愧的。可广大作协会员就是不投他的票。他未当上理事后,据唐羽在《余秋雨很想看这本书》中说:余秋雨从此竟反常地把由上海作协主办按期赠送他的《上海文学》、《萌芽》杂志原封不动地退还,由此可看出他的气量之小。 孙光萱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的这篇文章,虽本意不在揭露而在纠错,但实际上却让人们看到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一部分极为关键的真相,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对于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历史,余秋雨是怎样大胆地掩饰、改写、美化。由于余秋雨的叫板而引出的孙光萱的文章,等于把余秋雨逼到了墙角。不作任何回答,那等于是在默认。但要就具体问题反驳孙光萱,却又实在困难。于是余秋雨只得把面对批评时一再使用过的法宝再使用一回,即把孙光萱的动机归结为想出名,并且宣称“这种企图出名的强烈愿望使他的证言失去了公信力”。坦率地说,在继沙叶新之后,孙光萱又被余秋雨指控为想出名时,我感到了余秋雨的无奈,更感到了余秋雨的无聊。
孙光萱由此成为余秋雨最害怕也最痛恨的人。他在答北京《华夏时报》记者问时,含沙射影地把我和孙光萱比作“两个老纳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徐虹问“官司有无可能庭外调解”时说:“只有一个条件:古远清向法院揭发出向他提供那些诽谤材料的背后人物。然后,再由他来起诉那个造谣者,我有可能与古远清庭外调解”。
这里说的“那个提供材料者”,就是指孙光萱。孙光萱提供的材料,均是清查报告。说孙氏“诽谤”,其矛头是指向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班清查小组。正因为孙氏给我提供过材料,故在某种意义上说,告我就是告孙光萱,或告我就是为了恐吓孙光萱,以遏制孙光萱再披露真相,好让他从此闭嘴。
但孙光萱并没有被吓倒,他除为我提供证言,并无偿地提供了相当于给余“文革”错误作结论的夏其言致《新民周刊》的抗议信以及众多《清查报告》给我作证据外,还在官司期间写了《从“石一歌”谈到余秋雨》、《夏其言批评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不同的是,他的文章温柔敦厚,哪怕余一再攻击他乃至捏造各种罪名羞辱他,他均能正确对待,不以牙还牙。有人认为他患得患失太软弱,像余不止一次从人格上毁损他,碰到别人早就应战了。可他有自己做人和处事的原则:做老实人,决不说假话;以诚待人,决不做对不起历史、读者的事,决不趋炎附势。这样一来,“书生气”的确很重,开始他也是想真心挽救余,但余把他逼急了,也会豁出去的,他不怕恐吓之类的邪门歪道。他写的传诵一时的《正视历史,轻装前进》发表后,上海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写信称赞他的文章是“关于余秋雨现象讨论中最客观、最有说服力的。写这样的文章既要有阅历、见识,又要有勇气。”
这位上海作协副主席的话代表了广大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的心声。难怪上海作协换届选举理事时,余秋雨竟名落孙山。按他的知名度,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或副主席是当之无愧的。可广大作协会员就是不投他的票。他未当上理事后,据唐羽在《余秋雨很想看这本书》中说:余秋雨从此竟反常地把由上海作协主办按期赠送他的《上海文学》、《萌芽》杂志原封不动地退还,由此可看出他的气量之小。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