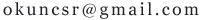卞一杰
合上《呐喊》,合不上的,是我们的“彷徨”。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正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
“没有什么病痛比精神麻木更为可怕的了,一个人无论体格如何强壮假如没有灵魂,就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
鲁迅是一个真猛士,直面人生,正视鲜血,七十多年了,他依然在奋然前行。这么多年过去了,鲁迅依然没有过时,教材里面处处有鲁迅,到处都有人在不厌其烦地歌颂着鲁迅。鲁迅如果真的过时了,我倒觉得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那表明:鲁迅提出的问题全部被解决了,“看客”在中国也不见踪影了,书本上再也找不到“吃人”这两个字了。如果教材只停留在背鲁迅文章上面,歌颂也仅仅停留在赞颂这个层面上的话,倒不如就象鲁迅的遗言里说的那样去做:“把我忘掉,然后过自己的日子吧”。倘不,那真是傻瓜。
把鲁迅和他的作品供奉着只知朝拜,就象存着巨额的财产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一样。鲁迅是我们的财富,而且到目前为止,象他这样的财富只有一个!
有多少人孜孜不倦地研究着《孔一己》中“大约的确”是否矛盾的问题,有多少学生苦苦背诵着《雪》里面的美文佳句,然而,令我痛心的是,每每街上一有打架争执,那些研究鲁迅的学者、熟读鲁迅的学生,往往都伸长了自己的“鸭脖子”,像被一只手被后面提着一样,拼命往前挤,争当“看客”。
鲁迅的文章没有金庸的小说那样有起飞跌荡的情节,也没有朱自清华美的文字,自主去读得人越来越少且不说它,就算有的人背着他的文章,“理解”了他的意思,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他的文章呢?懂得他的忧国忧民呢?鲁迅的文字是平淡的,然而“淡中知真味,常里识英奇”,他平淡的文字读完才感到回味无穷,静下来细想,良久才发现一种莫名的同感,良久才体会他深刻的含义。
现在的社会中,还有“祥林嫂”么?重要的其实不是有无祥林嫂,而是祥林嫂周围的人还存在吗?还有人拿着她的悲剧来给自己寻开心吗?的确,虽然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这样的问题或许还存在着,所以我们仍然需要鲁迅,需要呼唤鲁迅精神。记得读罢他的《啊q正传》,顿时觉得啊q似曾相识,细细一想,又惶恐起来,发现或多或少,我们身上都有啊q的影子。读完《狂人日记》,惊的自己一身冷汗,现在还有“人吃人”的事发生吗?想起当下的“三鹿奶粉事件”真正令我们愤怒和担忧。如果当我们读到《故乡》的时候,心中涌起的不再是因为老友的改变而难过,而是对文章真实性的怀疑,那时,或许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可信了吧。
“夜正长,路也正长。”鲁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夜却总是会过去的。鲁迅没有走完,但他明白:路迟早会走完。我也相信,即使我看不到路的尽头,我的后代一定会看到。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当人们能不仅仅是“读”鲁迅、“看”鲁迅、“背”鲁迅,当我们时时能够想起鲁迅笔下的人物并深刻反醒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能把鲁迅真正当作“民族魂”的时候,那便是路走完的时候。我希望,我能走上这条路。
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无路人走多了便成了路,成路后走的人更多了.鲁迅却没有告诉我们有路后的地上会怎样,这是他始料未及百算一漏的.现实告诉我们地上有了路人走多了便成沟了!
鲁迅在他的《故乡》里说: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的说法不一定是对的,起码算不上全对.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地上的路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知道他在从文之前是学医的,后来他为什么不走救死扶伤的“白大夫”之路了呢?也许你会说是因为他在日本电影院看了一场有中国人入演的记实片,的确,我起初也是这么深信不移的.但事实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小片段,就像鲁迅看到的电影片段一样.这只是鲁迅转意从文的一个小插曲,插曲的存在有它存在的价值.它的价值在于它使鲁迅看到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一条让麻木冷血的“龙的传人”走的思想之路.这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让真热慕于医科的鲁迅知道广漠的赤县虽有繁星般众多的炎黄子孙却走不出一条能御敌富强的民族之路.堂堂华夏大地缺的不是走路的人,而是缺能走出路的人.所谓能走出路的人指那一些人呢?鲁迅就是能在没路的地上走出路的人.在那个人且相食外忧内乱的时代何曾少过欲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热血爱国者,鲁迅是最具代表性的爱国“愤青”.稍接触过鲁迅文学的都知道鲁迅在热血青年时代去了小日本仙台学医.学的而且是骨骼学.那时的鲁迅天真地认为医道能救死扶伤就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个时代的爱国“愤青”都很天真.总以为学医就能就中国人民救广漠的赤县.所以从医之路成了那个时代爱国者的明智抉择.鲁迅也随了波逐了流到了日本研究人的206块骨头.忒天真无邪的.但中国的土地上没能让他们走出一条活路.当鲁迅不经意地看到日本崽屠中国人的记实电影时他犯懵了.那一可的他才涣然冰释醍醐灌顶,人走多的地方不一定就有路,没有针砭的路是不可能在中国广漠而荒芜的土地上走出来的.学医的中国“愤青”多如麻,但医者是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走出一条救国图存的路的.中国人的病不在肉体上,而是在思想上骨子里.只可惜鲁迅看到的是主观上的骨子病,他天真地认为治好了中国人骨子里的病中国有就有骨气了.他错了,错得彻底!如果他还一如既往执迷不悟地幻想在中国满目苍痍的土地上走出一条拯救中国的医学道路,那么他错得愚昧极了.那一段小插曲让鲁迅知道地上本没有路人走多了也不一定成为路,人走多了可能成为沟让那时代的话中国人越走越深越走越不能自拔.他毅然抛弃了和藤野先生深不可测的友谊弃医从文.他真正认识到中国人的劣根长在思想上而不是肉体上!
当《狂人日记》惊世之篇在一位曾致力于医学的文人笔下生花时,麻木的中国人你望我我望你,回到家也自恋地照镜子.这些人怕了,怕鲁迅写的狂人就是自己.当《孔乙己》轰隆于中国的上空时,麻木的中国知识分子胆颤了心惊了,你看我我看你,“孔乙己到底是谁?难到是我吗?”这样的问题成为了知识分子茶余饭后之事.当《阿Q正传》成为家喻户晓时,麻木的中国把“阿Q”示为“至宝”.你阿Q我阿Q地互相打招呼.……鲁迅还有很多很多让人不寒而栗的着作,他的一生走在一条不是众人都走的路.众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没能走出路但他却走出了.而且走得辉煌走得轰轰烈烈.现实的我们不能只抱着高考一条路,高考之路固然稳当,但走的人太多了,本有的路被走成了沟,后来者不再居上,高考的后来者面临的是名落孙山.何不梦回鲁迅之路,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走一条对社会有用的路!
在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冯骥才在《收获》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中认为,鲁迅作品的成功之处即在于独特的“国民性批判”,“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但这不过是“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舶来品,鲁迅从中受到了启发和点拨,却没有看到里面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冯骥才进而认为鲁迅没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被西方人认作经典的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东方主义”的磁场。这一度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鸣。陈漱渝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确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然而,“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否定性评价,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黄川在《亚瑟·亨·史密斯与东方主义》中重点分析了“东方主义”一词的含义和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详细情况,指出冯骥才把“东方主义”加之于鲁迅的头上是“轻率的、不科学的”。 由论争引发,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刻的领域。对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渊源,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以翔实的史料证实:鲁迅留日时期与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是受到当时弘文学院院长加纳治五郎与中国学者杨度关于国民性讨论的直接触动。潘世圣的《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认为,“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如梁启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有着多样的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王学谦在《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中指出,幼时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直接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并促成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程致中在《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关国民性的讨论的影响,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着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影响等等。袁盛勇的《国民性批判的困惑》则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源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他看到了我们国人的“古老鬼魂中”还有一个“我”,因而,“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他把自己拽进话语语场的同时,也一并让读者沉入其间,在自我反省中杀出一条生路”。尹康庄的《鲁迅的民众观》指出,鲁迅“致力终身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实践的逻辑起点”,是鲁迅对民众的“否定与肯定之间所形成的悖论”。方长安的《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和立人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深受日本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亦即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研讨会”的举行。这一学术会议是由汪卫东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和竹潜民的《中国国民性“密码”和“原点”探秘——兼与汪卫东先生商榷》争鸣文章引起。前文认为中国国民性“原点”和“密码”以“私欲中心”四字概括,后文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应是“自欺欺人”。陈越认为汪卫东的“私欲中心”失之太泛,竹潜民的“自欺欺人”不是“对国民性劣根性表现的深层原点的概括”。周楠本指出,“自欺欺人”说实际已包含于“精神胜利法”中,而“私欲中心”是和“精神胜利法”一样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因而“原点”和“密码”的提出并无多少新意。张恩和和林非都肯定了从“私欲中心”和“自欺欺人”入手探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积极意义,特别认为以“自欺欺人”为中心展开对国民性弊端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但对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他们都认为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绝对权力统治的结果,“在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范和限制下,怎么能不产生退守、懒惰、卑怯、奴性、虚伪巧滑、自欺欺人等各种各样的国民性”(张恩和语)。钱理群的论点有三:一、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不是外来思潮的移植;二、改造国民性问题涉及对民众的看法,鲁迅一向把民众分成两类,即“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和“在名教斧钺底下”失去了天性的“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后者;三、对“真”与“诚”的倡导,对“伪”的批判是鲁迅一生的命题。孙玉石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他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动因,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学传统拥有的“大爱与大憎结合的精神”,体现的是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因而孤立地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密码”与“原点”,“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孙玉石提出应当特别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这就是:“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他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思想的严密性。”追问
写点凡人的
追答自己上网查一下,有很多,节选合成就行了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向鲁迅致敬作文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 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 思想家和革命家,是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鲁迅时时刻刻的为人民着想,为祖国的命运着想。因此,鲁迅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岁岁月月,朝朝暮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刹那间...
有关鲁迅精神的作文
我心目中的鲁迅 谈起鲁迅,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吧!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鲁迅先生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岁那...
弘扬鲁迅精神作文1500字
鲁迅是最具代表性的爱国“愤青”.稍接触过鲁迅文学的都知道鲁迅在热血青年时代去了小日本仙台学医.学的而且是骨骼学.那时的鲁迅天真地认为医道能救死扶伤就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个时代的爱国“愤青”都很天真.总以为学医就能就中国人民救广漠的赤县.所以从医之路成了那个时代爱国者的明智抉择...
怎样发扬鲁迅精神?(200字作文)
作为中国人民为求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伟大代表之一,鲁迅是不朽的战士;他的作品和思想,是鼓舞人民从事新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永具生命力的精神遗产。鲁迅曾经用“风雨如磐”、“寒凝大地”、“万家墨面”一类沉痛的词句,描绘自己生活的时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鲁迅先生,令我崇敬作文900字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有无数的人因鲁迅的文章而彻底醒悟,可也有人企图让鲁迅先生“碰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依然拿起笔,坚定不移的写着,即使前方有无数的暴风雨,他也会说“:我所走的路,为的是全中国的人民,,他们不了解我,我没有怨言,我坚信,我所走的路,...
鲁迅的伟大的作文
独立的国家,他为了中国,为了民族,为了新中国的到来,她真是费尽了心血.今天,新中国终于成立了,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惜,他却永远闭上了眼睛...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我们更应该汲取鲁迅精神力量的领域,继续向鲁迅思想前进,迎接更多的挑战,为提高民族的精神文化境界而奋斗 ...
初中写人作文600字:我最崇敬的名人鲁迅
第一篇:我最崇敬的名人鲁迅 每个人都有心中的名人,可以是古人,可以是现代人,可以是明星,而我最崇敬的名人是鲁迅。他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人,我想大家都认识这位又是思想家、革命家的大文豪吧。我敬佩鲁迅的高洁。面对那四面八方黑暗的社会,他从不屈服,他是“彷徨”在黑暗中忍不住要要“呐喊”...
以“鲁迅精神的光耀”为题,写一篇800字作文
这是去绍兴以前,妈妈告诉我的鲁迅先生的一席话,我听了似懂非懂。 来到绍兴鲁迅故居,目睹了鲁迅先生犀利的眼神,想想妈妈对先生的尊敬,我不由地穿过小桥,一幢黑白相间的小楼扑入眼帘,“那就是鲁迅青年时代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妈妈几乎脱口而出,又兴冲冲地带我穿过一条幽深的长廊,来到一...
《致鲁迅先生》作文1500字
敬爱的鲁迅先生:这是数十年后的一个学生怀着敬仰之情写给你的信。我不知为何想要写信给你,恐怕是因为你让我懂得了一个简单却又深邃的道理吧。依稀记得小时候,我无意间从杂志上翻到了一页《题辞》,这便是我们的第一次“邂逅”。但这第一次似乎并不太美妙,因为从你瘦削的脸庞上、严峻的神情...
与鲁迅结伴同行作文
1、与鲁迅结伴同行 在我人生旅途中,鲁迅先生的形象一直是我心中的一道亮光。他笔下深刻的文字,对社会的独到见解,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都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指引灯。鲁迅先生以文字为武器,用锐利的笔触揭示社会的黑暗面。他以独特的讽刺手法,批判了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顽固势力。他的文字犹如一把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