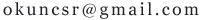第1个回答 2017-01-07
蒲公英都开到靡荼 文/微酸袅袅 引子: 深夜的时候爬起来翻林砚迪的网络日志,看他沿着黄河一路走时看到的山和水,拍下的那些很美丽的光影,听PachelbelsCanon,甜蜜宁静的忧伤. 常常会想起自己真的是幼稚啊,一把年纪了居然还在学小孩玩”忧伤”,可是,为什么,每次靠近有关林砚迪的种种,我都会被那种宁静绵密的感觉,深深淹没,万劫不复.. 林砚迪,他是我的伤. (一) 林砚迪一直说我是个骄傲帅气的小孩,从他第一次见我起. 那是95年的夏天,阳光灿烂到靡荼.参加校庆的演员在前台挨个走场,我坐在后台凌乱的道具中间翻着漫画. 后来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站起身转过头应了一声.然后——就看到了林砚迪.他站在我身后低垂的深红色幕布下,白底蓝格子的衬衣,中分的头发,样子正经得有点好笑. 他看到我,微笑,温润而内敛,带着礼貌的距离. 我扬着头冲他笑了一下,然后提着裙子跳过那些破烂的道具,匆匆忙忙的跑去前台. 林砚迪说白染墨,你知道吗?你那时回头一笑的时候,阳光正打在你的侧脸上,金灿灿的一片,笑容明媚得让人无法忽视.你握者竹笛,发丝贴在嘴角,提着裙子像小鹿一样跳过那些在你脚下匍匐的东西.我忽然就想起了王子.你像极了,童话里勇敢的小王子. 我说我当时穿着我唯一的一条白裙子,美丽的简直要冒泡——可是为什么在你眼里,我依然只是小王子? 林砚迪笑笑,垂下眼睑不说话.他总是这样,不想回答时就不说话,丢我一人在那里胡思乱想. 林砚迪,他是个坏蛋. 会认识林砚迪,是因为我闯了生命中第一个严重的大祸. 那时我不过13、4岁,热血沸腾的年纪.回家的路上被高年纪的学长勒索零花钱,我不给,就和他们扭打起来.那肢体的碰撞间,我不知怎么就拿起砖头砸破了其中一个的脑袋.我发誓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的血,像自来水一样哗哗的从那人的额头冒出来.其他人都吓得一哄而散,我握者砖头呆站在 那里,看受伤的人哭的鬼哭狼嚎. 林砚迪经过,在我面前看了我很久,问,你为什么还不跑? 我愣愣的将目光移向他,声音微微颤抖的说,我,我跑不动....... 砖头从我手上掉下来,砸在了林砚迪脚上.可是他的脸只是忽然扭曲了一下,却住没哭.他勇敢的捡起那块砖头然后拉住我,穿过行人跑得飞快. 林砚迪和我一直跑到近郊的小河边才停下,他气喘吁吁,然后把那块砖头用力掷到了宁静流动的小河里,激起很大的浪花. 我说你为什么把那块砖头扔掉? 林砚迪看了我一眼说你难道想带回去做纪念? 我窘得脸发热,狠狠瞪他,说,我以为你需要,所以才一路抓紧不放! 林砚迪走过来戳我的脑门,说笨~你不知道做坏事首先要做的就是消灭证据吗? 我后退一步,狐疑地看者他——此刻的他,一点都不像我当初见他时看到的温文模样. 我说,你是,林砚迪吗?那个红领巾永远挂的端端正正,头发永远中分的很整齐,做数学从来都不会错的林砚迪吗? 林砚迪又戳我脑门,说,笨~ 然后他就低下眼睑,不说话了. 那时的落日那么美,又圆又大又亮,像是没煮熟的蛋黄.小河宁静得像首诗,缓缓的流动,河边的芦苇在风里整齐的摇摆.14岁刚刚摘掉红领巾入团的林砚迪,蹲在我身边鼓着腮帮子吹蒲公英. 他拍拍我的头说许个愿吧,蒲公英飞走的时候会把你的愿望带的很远很远,远得可能会让神仙听到,然后你的愿望就有可能实现. 我嗤笑他说你真傻,居然相信有神仙. 林砚迪狠狠瞪我.我乐,飞起一脚把岸边躺着的一只烂釉子踢的老高.那个在天空中画出华丽弧线的物体,开心的笑.我说林砚迪你看,我脚力很厉害吧?你再敢瞪我我一脚踹飞你. 我低下头看到张大嘴巴瞪大眼睛的林砚迪.他看了我很久很久,久到我都快不好意思时他说,白染墨,原来你不是装傻,你是真傻. 我生气的大叫,却忽然发现那只烂釉子还躺在我脚边,而我可爱的脚趾头,正从粉红色袜子的小洞里很努力的探出脑袋来! 我愣了一下,然后哇的哭出声. 林砚迪不耐烦的说你哭什么啊. 我一边抽泣一边说,现在我怎么回家啊~(其实我当时哭的更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双破了一个洞的袜子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林砚迪说你真傻哦,当然是走回去咯,难不成不想爬回去? 可是脚会疼…… 那天,是林砚迪把我背回家的.我趴在他背上,咬着狗尾巴草不怀好意的说林砚迪,你觉不觉得我现在很像白马王子? 林砚迪撇撇嘴说,麻烦你在报名当王子前,减个肥先!我气得在他背上哇哇乱叫,可却拿他没辙. (二) 很多很多年后我问林砚迪,我说我们是不是太过晚熟,在13、4岁已经不算很小的年纪却把这样的斗嘴和小把戏,玩得如此津津有味? 林砚迪扬扬眉毛说,你可能是,我却不是.我当时只是觉得有个傻瓜很好玩,升学考压的我很烦,和你玩却会让我觉得那些事情离我很远. 我嘿嘿笑着说原来你曾经那么倚靠我摆脱生活的苦难.林砚迪不假思索的回击说,你还不是依靠我才逃脱”牢狱之女”? 我闯祸后的第二天,”白染墨用砖头行凶”的说法就穿遍学校.伤者的父母更是双双赶到学校要找我爸妈给个说法.而且高年纪那伙学长很不厚道的篡改口供,硬说我无缘无故打人.若不是林砚迪帮我作证,要不是基于他一直的好孩子形象,我还真可能就成为那桩冤案的可怜人士. 我扬起下巴用鼻子很大声的出气说哼!林砚迪,我这辈子都不会感激你的,你少做白日梦了! 林砚迪垂下脸笑,说,我从来就不要你的感激.你的感激,又不值钱. 我开始哇哇大叫,稚气的一如当年. 那时我已经十七岁,和林砚迪在同一所重点高中念高二.他读理我读文,分开在求实和从严两幢不同的教学楼,两两相望. 我说这楼,怎么造的跟牛郎织女似的啊,中间那湖就是那银河,学校怎么省钱连桥也不造啊? 林砚迪白了我一眼说,防的就是你这种伪织女,偷偷跑来勾引善良英俊的牛郎. 我说谁是牛郎啊? 林砚迪说正巧你眼前就有一个…… 他话还没说完我就不怀好意的鬼笑鬼笑.林砚迪回过神来,戳着我脑门大骂,你这个坏女人! 他居然脸红了. 17岁的林砚迪居然会为了这样一句不算太怎样的话而脸红?! 我忽然发现其实嘴巴很坏的林砚迪很纯情,而他纯情的时候,眼睛像星星一样好看得让我心砰砰跳. 林砚迪,我是说,我好象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喜欢你的. 因为我忽然发现这世上再不会有一个男生脸红时有你那么好看,也再不会有这样一个人戳者我脑门大骂你这个坏女人时,我还可以觉得那么开心. 林砚迪,你惨了,我喜欢上你了. …… 最后夏蓝多怀了孩子流产死掉了,林砚迪承受着所有人的误解,最后由于白染墨的误解,他终于崩溃决定离开学校.林砚迪的弟弟(喜欢白染墨的那位,忘了名字了.)去了日本,故事里的人物都上了大学. 后来白染墨才知道,当初那个让夏蓝多怀孕的是林砚迪的弟弟......只不过当天林砚迪把校卡借给了他弟弟,PARTY过后大家都醉了,他弟弟发现他和夏蓝多一起睡,匆忙中逃跑却把林砚迪的校卡落在了间...... 这个时候林砚迪已经是一名著名的撰稿人.林砚迪在采访中说,他曾经很爱一个女孩,在和她吹蒲公英时暗暗许愿要和她过一辈子.可是这个女孩最终伤他很深,所以在困境的时候他就会想这个女孩给他的伤,想连这种痛都可以然后挺过来,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受. 白染墨读他的博客,看他的文字,像所有喜欢他文字的粉丝一样,网名叫吹散的蒲公英. 林砚迪说,吹散,你的名字让我想起了过去的事情.(-=大概是这个意思) 她说她曾经伤一个男孩伤得很深,问林砚迪可不可以代他听.最后白染墨以粉丝的身份和林砚迪通了. "我说对不起. 我说我爱你." 林砚迪说,吹散,你的声音都是这么熟悉. 白染墨放下,泪如雨然后我就像所有在经营暗恋的小女生那样,开始有了甜蜜又沉重的心事,会无缘无故傻傻微笑,也会因为他的忽视而患得患失。 我甚至开始忌妒,忌妒所有可以整天正大光明的和林砚迪生活在同一个教室里呼吸同一片空气的女生——尤其忌妒那个个子比我高,长的比我好,声音比我动听,性格比我温柔,见林砚迪时间比我多的夏蓝多! 其实客观的说夏蓝多是个好女孩,若不是有林砚迪,我可能会很喜欢她——即使有了林砚迪,我在忌妒她的同时也欣赏着她。 森永爱画过一个“贫穷贵公子”,而夏蓝多就是现实版的“贫穷贵小姐”。她看起来那么美丽高贵修养良好,可是却不得不依靠助学金和奖学金才能继续学业。她一整个夏天只有一条洗的泛黄的白裙子和一件碎花衬衣、蓝格子七分裤可以替换。 可,仍是没有人可以比她更漂亮。 那时,整个学校的女生,都再没有人可以笑的比她更好看,让人明白世间种种美好,其实真的存在。 我趴在从严楼的天台上,看着经过楼下那条林荫道的林砚迪和夏蓝多。他们不知在讨论题目还是说着班里的事,脸上漾着愉快的笑,树影流水一样从他们年轻的脸上一寸一寸的滑过。 那是我见过的,最唯美的刺眼画面。 我想这是多么的不公平。我和林砚迪认识超过三年,可是他却从来都没有像对夏蓝多那样对我温柔微笑过;甚至在我发现自己喜欢他之后,他却还停留在当初逗嘴打闹的地方。 我想我和林砚迪之间可能隔着一段无法跨越的时光,我比他快了一步,所以我们无法手牵手合拍的向前走。 ——这个认知,真是让我无比的沮丧和难过。 可是,我是谁啊?我是白染墨,王子一样的白染墨。甩甩头发摆摆手,我很快就决定不去想那么麻烦的事。 中午在食堂吃饭照例又遇到林砚迪。他的物理老师拖堂,害他没到最喜欢的红烧狮子头。我像只狗狗一样叼着人间美味,冲林砚迪面目狰狞的笑。 林砚迪气的牙痒痒,乘我不注意硬是从我碗里抢走一大半的红烧狮子头。我气的大叫,我说喂,你有没有搞错?那上面有我的口水耶! 林砚迪看着我,一眨不眨。他说,这有什么关系。 我举着叉子的手就那么好笑的停留在半空中,摆着无敌猛女的造型,可是脸却一路红到耳根。 他眼神澄澈的说,这有什么关系。 是,这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自己龌龊的像头女色狼。 我埋头扒饭,头低的快要整个都埋到了饭碗里——我是说快要,因为在进行这个动作的同时我忽然发现,其实我的脸很大,很难整个都埋到碗里去…… 我又沮丧的想要哭。 林砚迪说你怎么越大越像个女人?不就是个红烧狮子头嘛,你有必要表现的好像丢了几百万?好啦,下午放学我请你吃冰激凌啦。 我想了想抬起头说好,然后眉开眼笑春暖花开。 放学的时候我在“银河”旁的小树下等了林砚迪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会从七月初七等到下一个七月初七时林砚迪他才出现。 他说对不起白染墨,我今天没法和你一起回家。夏蓝多她刚才出板报,从课桌上跳下来时扭到了脚,我要送她回去。 我瘪着嘴角一挥手说好啊,正巧阿卡找我打篮球。冰激凌可以改天吃啊,反正你欠我的。 林砚迪如释重负的说好。笑容温暖的好像快要融化我冰在眼底的泪。 我夸张的摆摆手,然后甩上书包去球场找阿卡“斗牛”。 林砚迪带着夏蓝多从球场边经过的时候正轮到阿卡进攻,我却直直的站在篮下,眼里只看的到林砚迪的身影。 夏篮多唯一的一条白裙子,飘起来时候原来那么好看,像世间最美的蝴蝶的翅膀。 等林砚迪的背影消失在校门口,我又回头看阿卡时,刚好篮球飞过来,打在了我的鼻梁上……然后我,血流如注。 阿卡那个笨蛋,没人拦他他居然也投不进,球反射回来时很热烈的亲吻到我。 我在球场上躺成大字形,阿卡在我旁边努力把纸巾搓成可以塞进我鼻孔堵住鼻血的小团。 我说阿卡,我也受伤了。 阿卡说我知道,你还伤的不轻,鼻子肿的像颗樱桃,血流的像小河。 我咯咯笑着说阿卡其实你还挺有文采的啊,比喻句使的可真溜。 我安静的望着头顶那片低沉的金色云朵,我说阿卡,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可怜? 嗯。 那,如果现在林砚迪看到我,他是会继续送夏蓝多回家还是改送我? …… 我看着那只停伫在篮筐上的孤独的燕子,自己回答说,他会说,阿卡,你送一下白染墨,她很笨啊,你千万不要让她在路上就流血流死了,我送下夏蓝多再去追你们。 阿卡担忧的望着我叫我的名字,他说小染,你不要这样…… 我把纸巾铺在脸上,然后,它很我飞速的回头用力瞪阿卡,他看着我当时肯定丑陋的很骇人的表情,没了声音。 我再鼓起勇气回头看林砚迪时,他已经走了。 阿卡说小染,事情变的有些糟糕。 我站起身,抹干净脸上的眼泪和鼻血。我说又没死人,糟个P! 然后我就很帅的甩上书包,雷厉风行的大步踏着夕阳回家。 我知道阿卡一直在我身后望着我,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出,我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心上的那种疼痛。 心痛的要死,肚子又好饿……真是屋漏偏逢下雨天。我一边走,一边又开始泪水涟涟。 第二天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中午吃饭时我还是和林砚迪在食堂为狮子头大打出手,放学后照样和阿卡玩“斗牛”——中午我打架输给了林砚迪,下午“斗牛”又赢了阿卡。一切都风平浪静,好像所有的所有都一如当初般和谐无常。 可是我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 我一个人走在安静的地下铁的过道里,掏钱的时候一元的硬币从我口袋里蹦出来,一路滚出去,跑了好远后才转了几个圈在一双黑色的球鞋边停下。我蹦过去捡钱,抬头,看到也正低头看我的黑球鞋的主人。 他安静的微笑,皎洁如月,王子般的高高在上。 我握着硬币站起身,感觉好像头顶上轰隆隆的裂开了一个洞。“黑鞋王子”长的可真像林砚迪啊。几乎是一样的眉眼和嘴角,连笑容的弧度都像是用量角器测定过似的。只是,林砚迪纯白的像阳光,他皎洁的如月光。 我忽然就笑起来,我说哈,你长的可真眼熟啊。 黑鞋王子眨眨眼,有些调皮的说,小姐,你以前都是这么追男孩子的吗?你的搭讪方式可真老土啊。 我愣了一下,然后就和他一起大笑起来。 黑鞋王子说他叫江臣希,我说我叫白染墨。然后我们一起搭地铁,一起去相同的目的地,一起闲闲的在小店聚集的街头闲逛,一起坐在透明的玻璃窗边,面对来来往往面目匆忙的行人吃巧克力圣代。 我一边吃冰激凌一边想这真是场美好的艳遇,然后又一边想一边努力控制口水的分泌量。 那个本会无聊的要死的周日下午,因为有江臣希的出现,开始变成一场有趣的邂逅。我从不否认我是好色又自私的女人,所以当看到和自己喜欢的男生有着相似面容的英俊男生,毫不犹疑的就绽开了笑脸。 可是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江臣希企图在昏暗的灯光中亲吻我的时候,我用力推开了他。 江臣希迷惑,他问为什么?我们不是玩的很好吗? 我甩甩头发又扬扬眉,我说是,我们玩的很好,可是,也仅此而已。谢谢你给过我这么一个有趣的下午,那会是我记忆中很美丽的一段回忆。 再见,江臣希。 江臣希起先是不说话,直到我走出很远后才在我身后很大声的笑,说,白染墨,你猜,我会不会轻易放过你? 我给他的回答是我骄傲挺直的背影。 我喜欢的是林砚迪,这一点,从来都没有模糊过,任谁出现,结果都是一样。这根本不是江臣希会不会放过我的问题,而是,我愿不愿放过自己的问题。 我是死心眼的小孩,这一点,连了解我如阿卡,都未必知道。 可是我却低估了江臣希。 和江臣希相遇又分别后的第三天,我就在我的位置上看到了又再出现的他。 他眯着眼笑着说HI,我亲爱的小墨。 我呆愣在那里,以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生错误,时空交叠,不该出现的人出现在他不该出现的地方。 可是江臣希探过身,横过我和他之间的课桌,一只手轻拍我的脸颊说,小墨,你没有在做梦——我只是动用了一点点我爸爸的关系,转学到了你班上。 我飞速的回头用力瞪阿卡,他看着我当时肯定丑陋的很骇人的表情,没了声音。 我再鼓起勇气回头看林砚迪时,他已经走了。 阿卡说小染,事情变的有些糟糕。 我站起身,抹干净脸上的眼泪和鼻血。我说又没死人,糟个P! 然后我就很帅的甩上书包,雷厉风行的大步踏着夕阳回家。 我知道阿卡一直在我身后望着我,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出,我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心上的那种疼痛。 心痛的要死,肚子又好饿……真是屋漏偏逢下雨天。我一边走,一边又开始泪水涟涟。 第二天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中午吃饭时我还是和林砚迪在食堂为狮子头大打出手,放学后照样和阿卡玩“斗牛”——中午我打架输给了林砚迪,下午“斗牛”又赢了阿卡。一切都风平浪静,好像所有的所有都一如当初般和谐无常。 可是我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 我一个人走在安静的地下铁的过道里,掏钱的时候一元的硬币从我口袋里蹦出来,一路滚出去,跑了好远后才转了几个圈在一双黑色的球鞋边停下。我蹦过去捡钱,抬头,看到也正低头看我的黑球鞋的主人。 他安静的微笑,皎洁如月,王子般的高高在上。 我握着硬币站起身,感觉好像头顶上轰隆隆的裂开了一个洞。“黑鞋王子”长的可真像林砚迪啊。几乎是一样的眉眼和嘴角,连笑容的弧度都像是用量角器测定过似的。只是,林砚迪纯白的像阳光,他皎洁的如月光。 我忽然就笑起来,我说哈,你长的可真眼熟啊。 黑鞋王子眨眨眼,有些调皮的说,小姐,你以前都是这么追男孩子的吗?你的搭讪方式可真老土啊。 我愣了一下,然后就和他一起大笑起来。 黑鞋王子说他叫江臣希,我说我叫白染墨。然后我们一起搭地铁,一起去相同的目的地,一起闲闲的在小店聚集的街头闲逛,一起坐在透明的玻璃窗边,面对来来往往面目匆忙的行人吃巧克力圣代。 我一边吃冰激凌一边想这真是场美好的艳遇,然后又一边想一边努力控制口水的分泌量。 那个本会无聊的要死的周日下午,因为有江臣希的出现,开始变成一场有趣的邂逅。我从不否认我是好色又自私的女人,所以当看到和自己喜欢的男生有着相似面容的英俊男生,毫不犹疑的就绽开了笑脸。 可是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江臣希企图在昏暗的灯光中亲吻我的时候,我用力推开了他。 江臣希迷惑,他问为什么?我们不是玩的很好吗? 我甩甩头发又扬扬眉,我说是,我们玩的很好,可是,也仅此而已。谢谢你给过我这么一个有趣的下午,那会是我记忆中很美丽的一段回忆。 再见,江臣希。 江臣希起先是不说话,直到我走出很远后才在我身后很大声的笑,说,白染墨,你猜,我会不会轻易放过你? 我给他的回答是我骄傲挺直的背影。 我喜欢的是林砚迪,这一点,从来都没有模糊过,任谁出现,结果都是一样。这根本不是江臣希会不会放过我的问题,而是,我愿不愿放过自己的问题。 我是死心眼的小孩,这一点,连了解我如阿卡,都未必知道。 可是我却低估了江臣希。 和江臣希相遇又分别后的第三天,我就在我的位置上看到了又再出现的他。 他眯着眼笑着说HI,我亲爱的小墨。 我呆愣在那里,以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生错误,时空交叠,不该出现的人出现在他不该出现的地方。 可是江臣希探过身,横过我和他之间的课桌,一只手轻拍我的脸颊说,小墨,你没有在做梦——我只是动用了一点点我爸爸的关系,转学到了你班上。 .............................. 我飞速的回头用力瞪阿卡,他看着我当时肯定丑陋的很骇人的表情,没了声音。 我再鼓起勇气回头看林砚迪时,他已经走了。 阿卡说小染,事情变的有些糟糕。 我站起身,抹干净脸上的眼泪和鼻血。我说又没死人,糟个P! 然后我就很帅的甩上书包,雷厉风行的大步踏着夕阳回家。 我知道阿卡一直在我身后望着我,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出,我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心上的那种疼痛。 心痛的要死,肚子又好饿……真是屋漏偏逢下雨天。我一边走,一边又开始泪水涟涟。 第二天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中午吃饭时我还是和林砚迪在食堂为狮子头大打出手,放学后照样和阿卡玩“斗牛”——中午我打架输给了林砚迪,下午“斗牛”又赢了阿卡。一切都风平浪静,好像所有的所有都一如当初般和谐无常。 可是我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