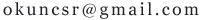所谓“夏尚尚,殷尚鬼,周尚文”,周朝一改前代的简鲁诡异风尚,而大力提倡人文文化,这主要是周公制礼之功。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一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参考1:
南怀瑾:
关于道家方士学术思想的渊源
http://www.white-collar.net/02-lib/01-zg/03-guoxue/其他历史书籍/专题类/文化/禅宗与道家/008.html
参考2:
驳胡适之《说儒》(钱穆)
http://www.oklink.net/a/0201/0128/shuoru/0006.html
南怀瑾
钱穆
受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现实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上古时代的国家想象并构拟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司马迁作《史记》,夏商周三个王国的兴衰便被描绘成大一统王朝的更迭。当然,后人的构拟事出有因,上古文献中早有此种倾向。《诗·玄鸟》中殷人称“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邦畿千里”;《诗·北山》中周人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其实,商周时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臣”,与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国家是不同的。
根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商王国时期的国家是一种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有的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方国联盟”,也有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部族国家”或“早期国家” 。所谓“部族”,是指由原始时代的部落组织衍变而来的、以血缘(族姓)联系为基础的社会集团,它是中国国家的早期形式。商王国时代的部族很多,卜辞中大多称之为“方”。商部族就是指子姓的殷人社会集团。
从殷卜辞反映的情况看,商邦与其他方国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特征:一方面是相互并存关系,另一方面商邦又凌驾于其他方国之上。先看并存关系。殷卜辞中有“比”字,林沄先生指出,这里的“比”均作动词用,是“亲密联合之义” 。殷卜辞中常见“王比某方伯”或“王比某伐某”的记录,如:“贞,王比兴方伐……”(《缀合》151)“乎比丹伯?勿乎比丹伯?”(《乙编》3387)“乙酉卜……令多子族比犬侯扑周甾?”(《前编》5·2·2)林沄先生认为,“卜辞确实反映出商代有许多方国和商王发生联盟关系,可考知者已有鬼、而、井、昜、丹、犬、暴、攸、望……等方。 绝大多数这类卜辞都明确地涉及征伐,所以说,商代是存在方国间的军事联盟的” 。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再去审读典籍中的有关资料,就不难发现当时方国联盟的情形。《诗·长发》述商汤伐夏桀的过程,“顾、韦既伐,昆吾、夏桀”。顾、韦、昆吾是夏王国的盟国。同样,《尚书·牧誓》述周武王伐纣,其中也有“我友邦冢君”。《诗·皇矣》叙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伐崇墉”。“崇”是商的盟国,而“友邦”是周的盟国。另一方面,商邦与盟国间是不平等的。卜辞资料表明,商邦不仅“比”其他方国,而且有时也“令”其他方国。如:“癸卯卜,宾贞……令沚■■方?”(《前编》6·60·6)“庚辰,贞,令望■■■方?”(《京津》4386)“癸亥,贞,王令囗侯伐……”(《金璋》368)这里的“令”,显然是一种指挥与服从的关系。同时,商王作为方国联盟的盟主,具有向盟国征取贡物、巡狩盟国境地、仲裁方国间争端和惩罚方国的权力 。 王国维早就推测说:“自殷以前……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 顾颉刚也说:“夏商所谓王,实则春秋所谓霸。” 今天看来,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周邦推翻殷邦的统治之后,建立了一个新的方国联盟——周王国。就大局而言,周王国与商王国的国家结构和性质并无根本差异,其不同主要在于“共主”的换替:周由小邦上升为“共主”国,商由“共主”国沦落为普通的邦国。周邦取得“共主”地位之后,当即与既存的方国确立了联盟关系,后人将此一过程称为“褒封”。所谓“褒封”不过是周王以天下共主的名义,与既存的异姓方国建立一种名分,组成新的方国联盟。其所异者,周代文献中大多将这些方国称之为“诸侯”。与此同时,周人还“封建”了一批同姓诸侯国。周人为什么分封同姓诸侯国?传统的说法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种解释虽可说通,但也有问题。因为周人的分封制度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而不衰,不但王室行分封,诸侯也行分封,甚至“大夫有贰宗”。单纯用“藩屏”之说作解,显然缺乏说服力。诚然,分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从商周历史的宏观过程看,分封也与部族人口的不断衍生相关,是部族殖民的政治化。它源于氏族时代的氏族组织制度。
大体说来,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周人分封呈现为两个阶段:西周时代是“天子建国”;春秋时代是“诸侯立家”。从部族人口分衍的角度看,“诸侯立家”是“天子建国”的下延和再版。然而,在当时“王土”、“王臣”观念下,王国、侯国、大夫之家具有大致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宗族政权特征。
天子王国,是以王族为核心构建的最高政治实体或国家。名义上,王统治天下;实际上,王主要统治“王邦”。这种“王邦”与“王天下”的政治格局被人们称为“内服”(王畿)和“外服”(畿外)制度。周代的“内服”、“外服”秩序展现为一个逐渐衰变的过程。西周前期,王朝对外服诸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量。在周初的诰命中,周王对诸侯百般教诲,指示他们服从王的指挥,“勿替敬,典听朕告”(《尚书·康诰》)。周康王在即位典礼时就训示道:“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告。”(《尚书·顾命》)当时,许多诸侯国君都参加了康王的即位大典,表示坚决服从周王的调遣,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同上)到春秋初年,此种盛世已不复存在,“周郑交质”乃一显例。其原因,自其表言之,是诸侯坐大;自其里言之,是宗族组织的成长壮大。宗族政治的基础是宗族组织。在氏族制度下,一个氏族的人口发展到一定数量,就会从中衍生出新的氏族,原来的母氏族则成为胞族 。宗族组织作为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氏族组织的这一特征。周初,王邦强大,新封的侯国力量微弱。后来,诸侯国力量不断壮大,而王邦却由于不断的分封发展较慢。当诸侯国与王邦力量相互制衡的时候,彼此间的冲突在所不免。“诸侯争霸”与王国代兴有相似的一面。从宗族政治的内部结构看,政权的主体是宗族贵族,在王邦是王族。在王族内部,又进一步凝聚到“宗主”身上。在周王室内部,对国家政权的厮夺直接体现为对“宗主”身分的争夺。春秋时期王室的内乱多导因于此。宗族政治的主要对象是庶众,是贵族对庶族的统治,宗主对庶民的统治。《诗·国风》中的一些诗篇展现了庶民对贵族的怨忿情绪和依存关系。对异族来说,周王族与他们虽无血缘联系,但却有宗教伦理关系。在商周宗教信念体系中,王被认为是上帝的嫡系子孙,而普天下的人们都被认为是上帝的子民(等级身分较低)。因此,自上帝的角度而言,王族与异族、王与异族人民之间有一种神授的“准”血缘纽带。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王族是上帝的“选民”,代表上帝统治天下。周王国所谓“内服”,实质上就是王邦——以王族为核心的政权和国家。
诸侯之国,是以公族为核心构建的二级国家政权和政治组织。从诸侯初封时的情形看,要举行册封仪式,授民授疆土,封国的主要官员也要由周王册命。《左传》僖公十二年记齐相管仲到王室觐见,王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推辞道:“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陪臣敢辞。”《礼记·王制》更说:“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于此可见王廷对诸侯国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预。诸侯国要对王朝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派兵助战、纳贡、朝觐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对一个既存的诸侯国来说,它的内政并不受王朝制约,在君位的继承、封立大夫、对具体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处理等方面,侯国都有自主权。在侯国内,公族是政权的主体,是根本;在公族内,由谁任宗主执政,是末节。尽管公族内也发生争夺君位的厮杀,但万变不离其宗,权柄必定落在公族之内。一旦这一原则被破坏,便意味着一个公族的沦落和国家的覆亡(或易姓)。“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都是例证。诸侯国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独立性,是因为有宗族组织作为基础。同周邦与侯国的关系相似,在诸侯国内主要是侯国与大夫之家的关系,直接显现为国君与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我们今天往往过多地注意到国君与大夫之间政治关系的一面,而当时的人们更看重宗族关系。铜器铭文中有规律地出现的赞颂祖先、祈求“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的词语,都反映出宗族组织和宗族利益的重要。诸侯国既独立,又与周王保持形式上的臣属关系当时政治结构方面的突出特色,是宗族政治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看,周代的同姓(或婚盟)侯国与商代的异姓方国相比并无大异,或者说大同小异 。
大夫之家,是以家族组织为核心构建的基层政权和隐性的国家。“诸侯立家”大致盛于西周后期。在较为可信的西周中前期文献中不见“大夫”之称 。 前已述及,“诸侯立家”既是政治行为,也与公族组织人口膨胀有关,此种情形与周初“天子建国”相似。“诸侯立家”有捍卫公族的政治意义,大夫之家是作为公族的“枝叶”而存在的。最初虽也“授民授疆土”,但从表面上看并不具备现代概念的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注意到周代的国家有王国和诸侯国,这虽比《周礼》的“王国”模式前进了一步,但仍未注意到大夫之家具有相对意义的国家性质。其实,诸侯国由周初围着周王团团转,到春秋初年自行其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大夫之家的情形同样如此。到春秋后期,许多大夫政权非但不听诸侯国君指挥,而且同诸侯国君分庭抗礼,几乎形成完全独立的国家政权。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三桓弱鲁”与“周政交质”没有质的区别,“三家分晋”正是“诸侯称霸”在一国之内的续演。李启谦先生对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之家作了较为具体的研究。他指出,在整个春秋时期,鲁国一直存在着很多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组织,粗略统计不少于15家。他们与国君保持君臣关系,但有很大独立性。(1)各家族“宗主”由自己确定,“宗主”是当然的大夫,因而,鲁君事实上并不干涉每个家族由谁来出任卿大夫。(2)大夫之家拥有城邑作为根据地。卿大夫在国都内建筑馆舍是为了谋政方便,真正的老窝是封邑。季孙氏有费邑,叔孙氏有郈邑,孟孙氏有郕邑。封邑内的臣属由家族自己安排,国君不问。即使邑宰发动针对大夫的叛乱,国君也不管。(3)家族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大夫之家的武装由家族成员及封邑内庶众组成,有很大独立性,听大夫指挥,鲁君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很像西欧中世纪所谓“臣下的臣下不是我的臣下”那种政治局面。正因“家”的武装是独立的,才有可能出现“家”与“国”对抗、大夫驱逐国君的情形 。
由上述王国——侯国——大夫之家相互关系可知,周代国家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具有方国联盟的性质;另一方面具有贵族等级君主制色彩。造成这种历史局面的深层原因是宗族政治,是血缘国家。血缘(或宗教伦理)犹如一条锁链,将整个王国天下的秩序纽结起来。忽略当时的族组织,就难以深刻理解当时国家的特殊性质。
的特殊性质。
二、国家元首:族长与教长
商周时期血缘组织与国家政治组织的契合,使当时各级族组织的首脑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他们不仅成为世俗权力的拥有者(族长),而且是宗教权力的拥有者(教长)。所谓“教长”,是指在宗教组织内对信仰有最高的解释权、对宗教事务有最高的裁决权的人。商周时期对宗教事务的裁决权突出体现在主祭权上。具体而言,商周王国的国王作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拥有最高的、绝对的宗教权力;诸侯国君作为侯国内宗教组织的领袖,既是侯国祖先神的代表,又是国王的臣属,是相对意义上的教长。各级君主的身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既是世俗社会的统治者,也是宗教事务的裁决者。当时的人们把这种合二而一的社会身份称之为“宗主”或“君主”。
为了表示自己特殊而至高无上的地位,商王自称“余一人” ,以示与苍苍众生有别。“余一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
第一,商王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在当时的“世界”上,商王被认为是上帝或神界在人世间的“唯一”最高代表,他是上帝的嫡系子孙,是上帝的使者。在后世传颂的《汤誓》中,商汤伐夏桀,他宣布诰命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桀残暴不道固然不合情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并非任何其他的人都能自称受上帝使命讨伐夏桀,只有商汤具备这种资格:他口含天宪,使命人间。这不仅是商王的自诩,而且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商代中后期,由于某种原因,殷人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在迁都过程中,殷人遭受了种种艰难困苦,商王盘庚因此受到严厉的责难。无奈之下,他向人们摊牌说:“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何虐朕民!……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予迓续乃命于天。”(《尚书·盘庚》)这一段诰辞表明,盘庚不但被认为是上帝的使者,而且是祖先神的代言人,是天界的化身。无论神对商王本人的惩罚,还是对部族群众的惩罚,其圣旨唯有通过商王本人方能得以传达。从实际情形看,数以万计的甲骨卜辞反映出的商王向上帝、先祖、其他各种神灵占问吉凶、祈求福佑的情形,正是商王这一身分的生动体现。
第二,商王是王国的最高教长。商王不仅是上帝的使者,而且是王国内最高的教长。有资料表明,商王不仅是占卜活动的主体,而且是庙祭活动的主体。先看占卜活动。殷墟卜辞中的王室卜辞可以见到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在通常情况下,由负责占卜的官员代商王例行占卜。例如:“乙巳卜,■贞,王勿其子■?”(《缀合252》)“戊午卜,■贞,王从沚囗伐土方,受又?”(《后编》上·17·5)“壬辰卜,贞,王田于■,往来亡灾?”(《前编》2·38·4)这里,占卜活动虽由贞人主持,但从卜辞内容可以看出,占卜的主体是王,而不是贞人。另一种情形是,王直接主持占卜,即所谓“王贞”、“王卜贞”辞例。例如:“戊午卜,王贞,勿御子■,余勿其子?”(《金璋》415)“戊辰,王卜贞,田率,往来亡灾?”(《前编》2·43·3)“戊申,王卜贞,田■,往来亡灾?”(《前编》2·16·1)王亲自占卜,这直接表明商王是占卜的主体。传世文献从另外角度反映了这一情形。《尚书·盘庚篇》记盘庚解释迁都原因时说道:“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这明确地告诉我们,遇事占卜遵从龟旨,这是商代的制度。商王作为卜主和贞主,是真正的占卜主体,这是当时人所共认的事实。所以,《尚书·君奭》记周公旦追述商代情形时说:“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卜官贞人虽众,但真正的主人是作为“余一人”的商王。同样,当殷人的统治出现危机时,人们认为是王的占卜权或贞主资格发生了危机。《尚书·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 格人元龟,罔敢知吉。’”所谓“格人元龟”,是说上天把占卜资格授予别人,天命转移了。失去天下教长的神圣地位,当然是“不吉”了。再看庙祭活动。文献所见,殷人在宗庙中的祭祖活动十分频繁,祖庙内的祭祀活动的主持人是庙主的嫡系子孙。就祭祀成汤和其他直系先王的活动而言,主持者正是时王——汤的嫡系子孙。《诗·商颂·那》:“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诗·商颂·烈祖》也吟颂道:“来假来享,降福无疆。顾予烝尝,汤孙之将。”所以, 商王盘庚理直气壮地说:“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尚书·盘庚》)参照卜辞反映的商王祭祖于宗的有关资料,情况更是昭然。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商王具有十足的教长特征,是他主宰着王国的宗教生活。他的权力和地位被认为是神授的,他所从事的每一项活动都被看作是在神的庇护下完成的。人民服从于王,是因为人们要服从神灵的意志。另一方面,商王又是现实的君主,是世俗的统治者。商王在打着神圣旗号的同时,无时无刻不赤裸裸地暴露出强权统治和对悖逆者的残暴镇压。此种情形,人们论述甚多,不必赘言。总之,无论是王权利用了教权,还是教权培育了王权,二者在商代始终共生并存,相得益彰。
周代的情形与商代基本相同,周王仍是作为天下最高的君主和教长出现的。由于周代的文字资料比商代丰富,因而能更全面地反映出周王身分的实质。
在周人的天国境界里,上帝是最高的主宰,其下有诸多自然神和祖先神。对上帝的敬畏,便意味着对神界的恐惧;上帝的使者,便是天国的使者。这个使者肩负着向人间传达上帝旨意的使命。周人把这种宗教使命称为“承帝事”或“绍上帝”。《尚书·多士》记周公旦对殷遗民宣布说:“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尚书·召诰》记召公对殷人和周人说道:“有王虽小,元子哉!……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对现实君王来说,“绍上帝”是极为沉重的宗教责任,是任何他人不得替代的神圣使命。《尚书·金縢》记周初武王生命垂危, 周公旦令史官祈祷天界的太王、王季、文王说:“惟尔元孙某(武王),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武王)有丕子之责于天。”所谓“丕子之责于天”,又被周人称为“配天”。《诗经·下武》说:“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所谓“承帝事”、“绍上帝”、“配天”,说穿了就是代表上帝统治人间。这种代表身分充分显示在周人盛赞的文王受命说中。由于“受命”,周王取代商王成了上帝的使者。《诗·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尚书·文侯之命》:“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惟是上帝,集厥命于文王。”由于“受命”,周王成了世俗社会的君主。《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王对土地的主权和对人民的统治权来自上帝或上天。普天下莫非王土、王臣,是因为人们认为普天下莫非帝土、帝臣。王被看作是帝的“全权代表”。《诗》中的某些篇章生动地描述了周王作为“百神”的主祭人和卜主的情形。《文王有声》道:“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两个“维”字,把权力和意志维妙维肖地揭示出来:占卜权属于“王”,最高意志反映于“龟”。《卷阿》:“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百神而主矣”,“岂弟君子,四方为则”,“岂弟君子,四方为纲”。毛传认为,诗的“君子”是指成王。所谓“百神尔主”,是说天子或王是百神的主祭人。《云汉》记述了周晚期的一次大旱灾,民不聊生,普天哀痛:“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不殄禋祀,自郊徂宫; 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毛传认为,诗中的主人是宣王。从诗文看,周王遍祀群神,行毕郊祀行祖祭,祭祀对象有上帝、后稷、旱魃等。周王作为这一系列宗教活动的主祭人,在诗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周人赞颂祖先的庙堂诗中,周王唱道:“我将我享,维牛维羊。”(《诗·我将》)而在一般的诗歌中,人们歌颂:“中田有庐(芦),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诗·信南山》)“曾孙”是宗主,是周王。他把人们献来的芦、瓜献祭先王,祈求先王庇佑。上述诗篇明白地揭示出,作为“曾孙”的“我”是祭祀活动的主人。从《尚书》中的资料看,周王是占卜活动的主体。《尚书ž大诰》中周公旦追述说:“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只有王可以代表国家用卜,这与《诗·文王有声》的诗文可以相互印证。周公旦接着说:“予……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周公旦用“大宝龟”,是因他“摄政”行王事,是占卜的主人。《尚书·洛诰》完整地展现了周成王的一次隆重的祭祀活动:“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文献记录这次祭祀活动有精确的时间、地点、祭祀对象,参加人员虽众,主祭人只有成王一人。甚至到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伐楚,管仲声讨楚人的第一条滔天大罪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左传》僖公四年)。可见,“王祭”是当时人所共知的规定。
周代行分封之制,授民授疆土,建立了不同等级的政权(有限国家)。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无论是“国”还是“家”,所取得的民和土都具有神授的性质;而且,正因为诸侯、大夫具有天然的、神授的资格,他们才得以受民受土,建立起不同等级的国家组织。
首先,诸侯是侯国的君主和教长。大量资料表明,在每一个诸侯国中,诸侯国君作为神授的统治者,拥有绝对的、唯一的主祭权。在君权与教权这两种权力上,教权比君权更深刻,更反映当时权力的本质。任何他人都不得分割或侵犯国君的主祭权利。下面我们以春秋时期的鲁国为例予以说明。《春秋》经传所记鲁国的一切重要祭礼活动,其祭祀主体都是时君。例如:
(1)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春秋》僖公八年)
(2)鄋瞒侵齐,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左传》文公十一年)
(3)九月辛丑,用郊。(《春秋》成公十七年)
(4)夏,诸侯如楚。鲁、卫、曹、邾不会。曹、邾辞以难,公辞以时祭。(《左传》昭公四年)
(5)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春秋》昭公十五年)
君有事于庙。(《公羊》同年传)
君在祭乐之中。(《谷梁》同年传)
(6)公曰:“君(晋侯)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 将使归粪除宗祧以事君……”(《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1)(3)(5)《春秋》所记虽未言及祭祀活动的主体是何人, 但这在当时人们看来是不言自明的,故《传》谓之“君”;(2)所记“公卜”, 占卜的主体是鲁文公;(4)所记“公辞以时祭”,时祭的主体是鲁昭公;(6)所记昭公自言“粪除宗祧”,更是不释自明 。
其次,大夫是封邑内的君主和教长。作为周王国最基层方域的君主,大夫也具有教长的某些特征。在春秋时代,“政”与“祀”并存,人们习惯于把一个大夫政权的存在称为“祀”。在宋国,国君讨伐向魋,向巢惧而奔鲁。 宋君派人劝向巢留下,说:“寡人与子有言矣,不可以绝向氏之祀。”(《左传》哀公四年)延续向氏祖庙的烟火不断,就是保留向氏政权。大夫华耦到鲁国访问,他对鲁文公说:“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左传》文公十五年)这里把继承大夫政治权力称为“承祀”。在卫国,卫人讨伐宁氏之党,石恶奔逃晋国。“卫人立其子圃,以守石氏之祀”(《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在郑国,《左传》昭公十六年记子产说:“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这里把问题说得更明确,同时指出了孔张是“嗣大夫”并“祀于家”这双重角色。所以,杨伯峻注云:“立于朝谓朝有官爵,祀于家谓家有祖庙。”文献中此类事例虽不太多,但事实同样很清楚,大夫不仅是“家”的君主,而且是“家”的唯一主祭人。
综上,在周代的“封建”制度下,天子是绝对意义的君主和教长,他的意志具有政治上的最高权威,他对上帝的意旨有唯一的解释权,对宗教活动有最高的仲裁权。诸侯和大夫是相对意义的君主和教长,他们的意志在各自的封域内有政治威权,对封域内的宗教活动拥有主祭权和仲裁权。因而,周代的天子、诸侯、大夫与秦汉以后国家的各级行政官员不同,与秦汉以后宗教的各级僧官也不同。他们是政、教合一的领袖。顾颉刚先生曾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古代所谓唐虞之世者,是否有类于印度,今不可知;或君主既属婆罗门等级,以祭司身分执掌政权,亦不可知。今所可知者为商周,其时君主或称‘帝’,或称‘天王’,表示其地位超乎人而近乎天” 。古代印度的婆罗门种姓虽然高贵,教权虽然隆盛,但同中国商周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相比,不免黯然失色:后者不仅有圣达的神性,而且有世俗的威权。当然,商周时期的各级族长虽是宗教领袖,是教长,但不是祭司。作为具体的执事人员,祭司是教长的臣仆。
三、政府组织:行政机构与祭司机构
在商周部族国家状态下,各级族组织的领袖不仅是政治首脑,而且是宗教领袖,一身而二任。若使各级君主独自完成上述双重职责显然不可能 ,他们必须组建起一套机构方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使命。正是这样一套政府机构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上古国家的诞生。
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朦胧的记忆中,上古时代国家的职官分为两大系统:一个是神职系统,一个是政治系统。《国语·楚语下》记观射父论“绝地天通”说,古者,“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又说,颛顼之时“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北)正黎司地以属民”。在这里,神职系统与政职系统并存,而以神职系统为先。《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从表面上看,上述“五鸟”、“五鸠”分别是天官和民官,天官司星历,民官司民事。但是,在远古时代,星历之事与现代天文学并非同类概念,其背后隐匿的是星相筮卜之类的活动,是神务。再看《礼记·曲礼下》:“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将朝官划分为“天官”和“五官”,“天官”典司“六典”,即司理宗教活动;“五官”典司“五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商周宗教思想国家元首
在商周时期,国家和社会的组织结构中,血缘与政治紧密结合,使得各级族组织的首脑,既是世俗权力的族长,又是宗教权力的教长。他们通过主祭权来行使对宗教事务的裁决权,如商王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而诸侯国君则是侯国内宗教事务的领袖,对祖先神和国王效忠。这些君主的身份既...
商周宗教思想分封
在商周的宗教观念中,王被视为上帝的直系后代,而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尽管等级有别。从神学角度看,王族与异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准”血缘纽带,基于王族被视为上帝的“选民”,代表上帝统治天下。因此,周王国所谓的“内服”,实际指的是以王族为核心的王邦,即政权和国家的核心区域。
商周宗教思想政府组织
在商周时期,国家结构中,政治与宗教的融合是显著特征。各级部族的领导者既是政治领导者,也是宗教领袖,这种双重身份促使他们需要建立一套专门的组织来管理。这套政府机构的建立,象征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上古国家的官制记忆中,主要分为神职系统和政治系统两个部分。《国语·楚语下》...
商朝时宗教信仰是什么
巫术是人类最原始的宗教形式。从古史数据和人类学理论来看,三代以上,三皇五帝时代的巫觋已比较接近于沟通天地人神的萨满。而夏商周三代的古巫虽带有上古巫觋的余迹,但已转变为祭祀文化体系中的祭司阶层,其职能也主要为祝祷祠祭神灵,而非巫术。三代古巫的记载出现在文字产生之后,这时中国文化已经历...
商周宗教思想基本特征
在商代,商邦与其他方国的关系呈现出双重特性:并存与从属。根据殷卜辞中的“比”字,这是一种象征亲密联合的动词,如“王比某方伯”或“王比某伐某”,表明商代存在众多与商王结盟的方国,如鬼、而、井、昜等,这些盟约通常涉及军事行动。卜辞中还反映出,商邦与盟国之间的关系并非平等,商王拥有对...
商周宗教思想基本信息
近年来,学者们对商周时代的国家结构有了新的理解。他们认为,商王国时期是众多方国的联合体,有人称之为“方国联盟”,也有学者将其视为“部族国家”或“早期国家”。部族,源于原始部落的演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集团,是早期中国国家形式的基础。商王国时期存在着众多的部族,卜辞文献中常以“方...
商周宗教思想的特点
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
商周宗教思想诸侯之国
诸侯之国,是一种以公族为核心的二级政治实体,由周王通过册封仪式确立,授予土地和人民,主要官员由周王任命。例如,《左传》记载齐相管仲在朝见周王时,虽被以上卿之礼接待,但管仲谦辞表示自己只是天子的下属。《礼记·王制》则明确指出,大国的三卿职位皆由天子任命,显示出王廷对诸侯国政治的干预。...
夏商周三代的宗教思想是什么?
夏商周三代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巫术,夏朝至今到底是不是存在还不知道,商代崇尚鬼神之事,用鬼神来威胁人民,达到统治的目的,从商代遗留的一些青铜器上面的纹饰和文字记载均可以知道,名为饕餮的怪物就是商代人创造出来的。而到了周代这种情况相对缓和,并且周代也是相对于其他朝代来...
宗教而言如何理解王国维所说的商周间的变革是叫文化废而新文化兴_百度...
王国维所说的商周间的变革是指商朝和西周的更迭,这一时期的变革在宗教方面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商朝是以祭祀为中心的宗教形式,而西周则开始出现以崇拜天地为核心的宗教思想,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向天人合一的方向发展。王国维认为,这种变革导致了旧宗教的衰落和新宗教的兴起,从而使得文化在宗教方面...